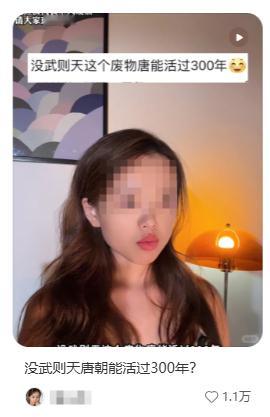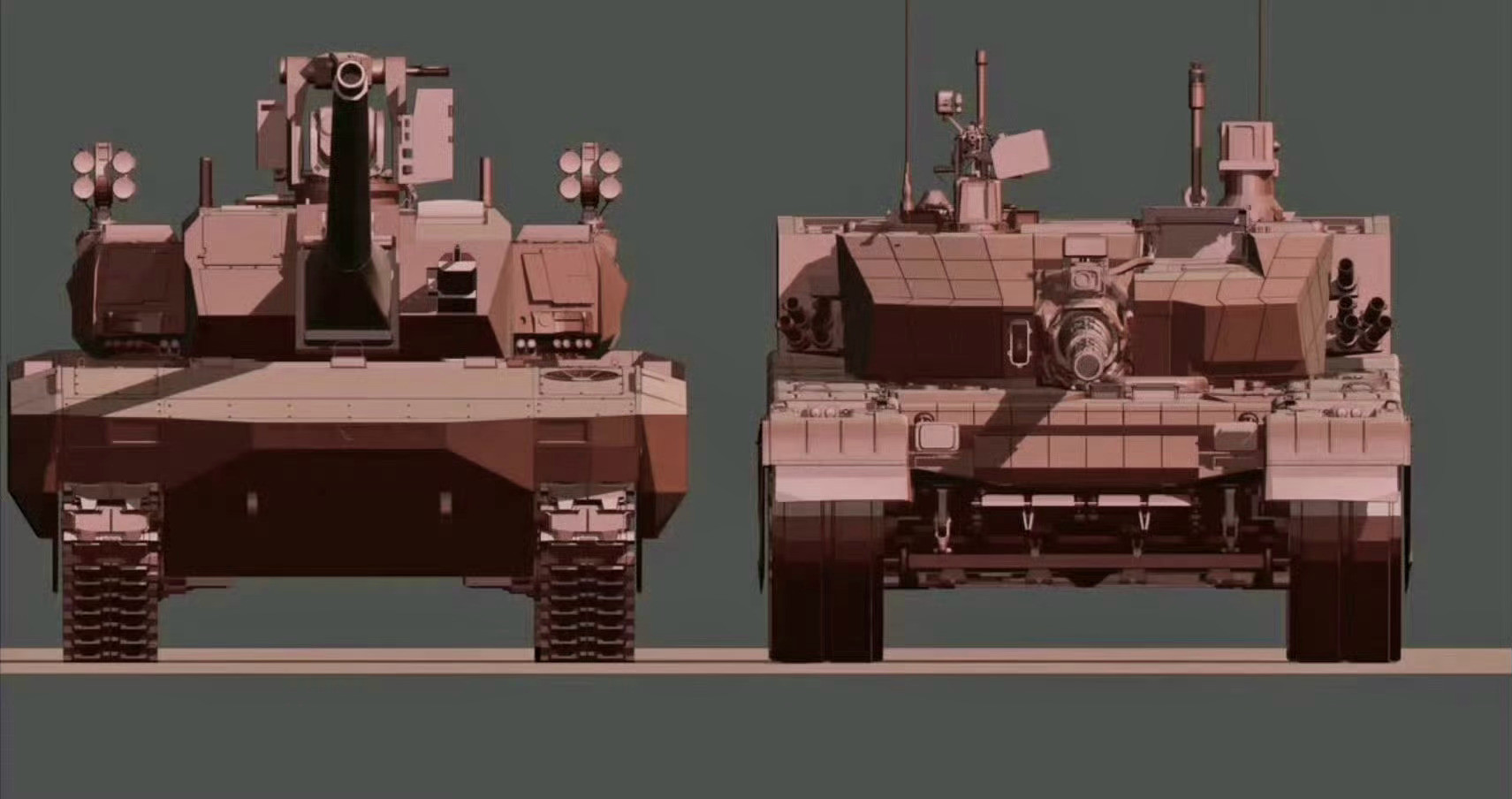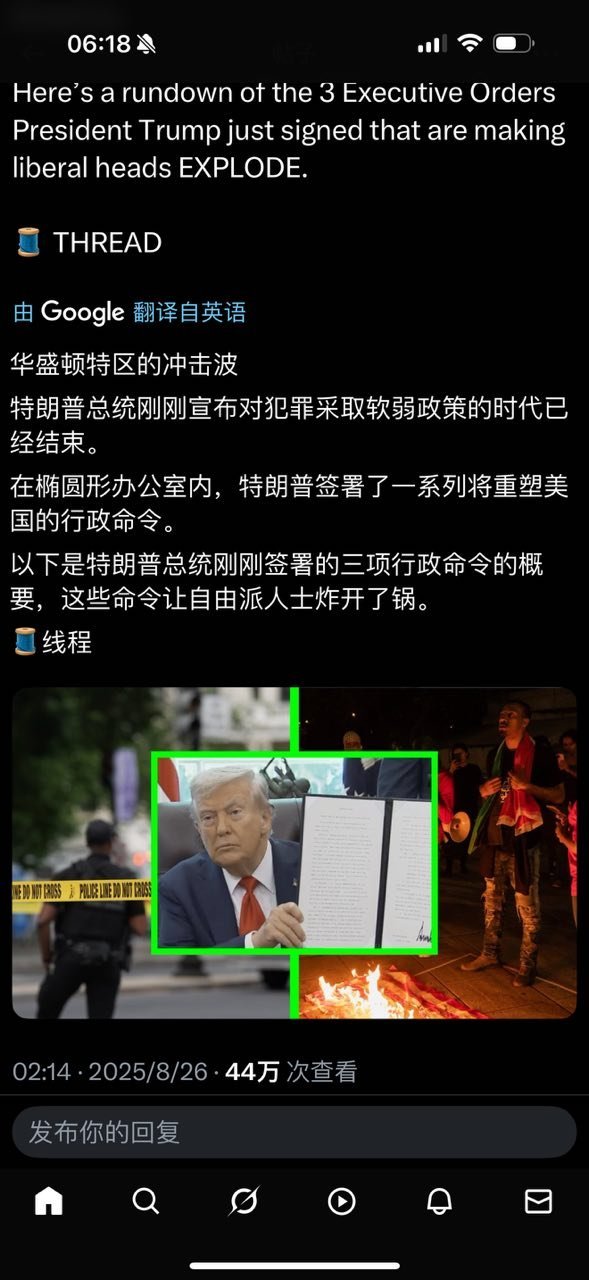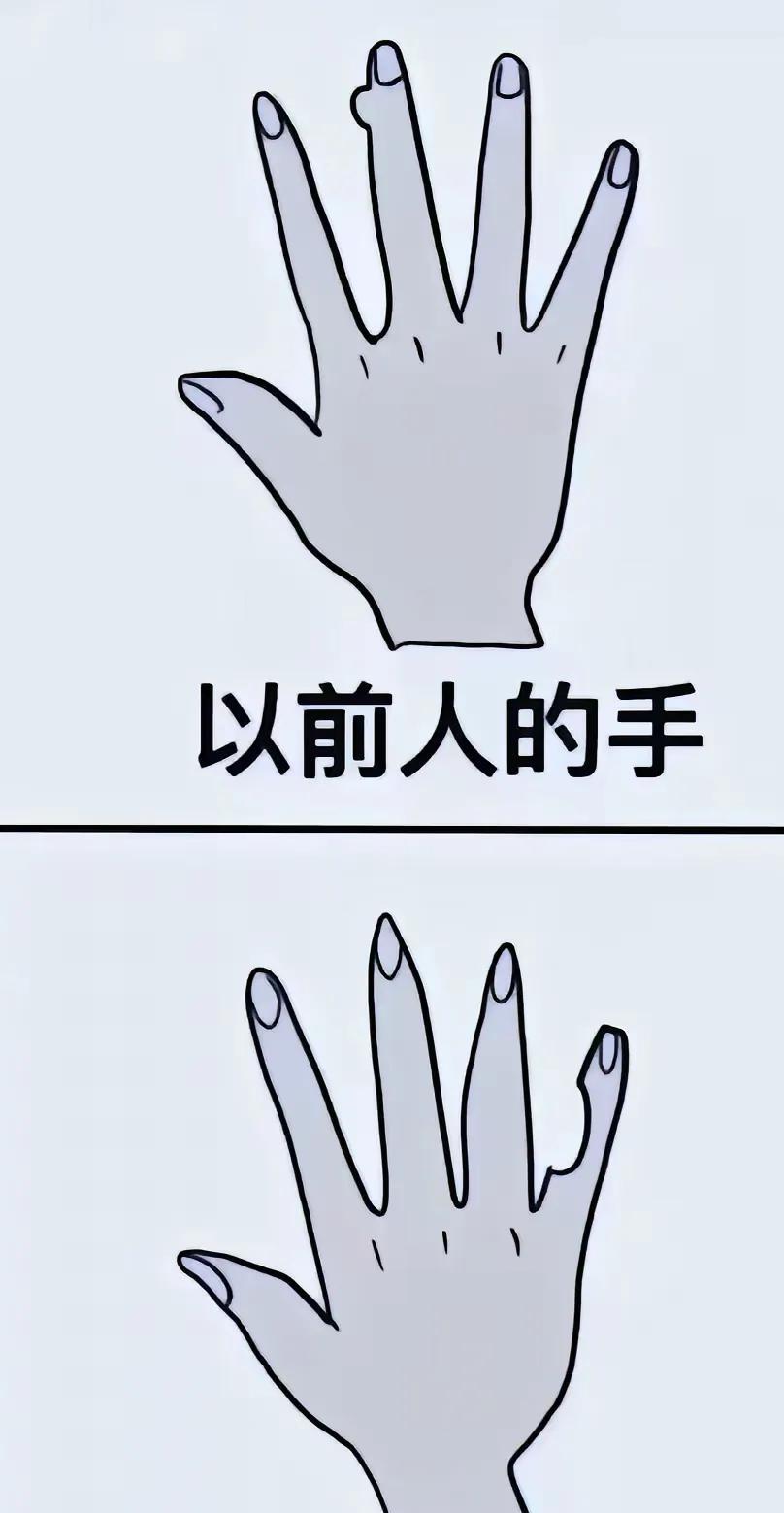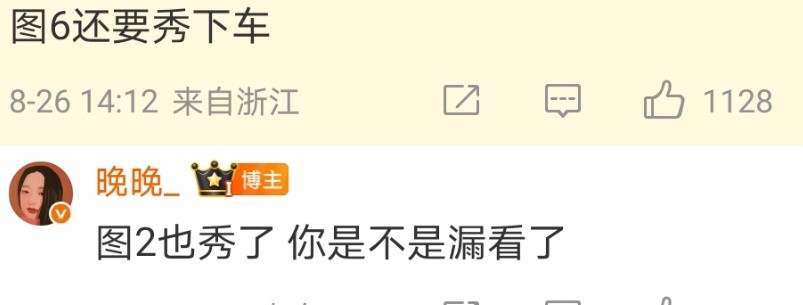刘震云:“做好事的,不一定就是好人;干坏事的,不一定就是坏人。好人坏人,轮不到自己定调,权柄握在谁手,谁便捏着这生杀笔砚。” 自古卑躬屈膝者,头顶“良善”名号;揭竿而起者,背上“奸邪”烙印。忠奸二字,无非是权杖之影,掌权者说黑是白,白便成黑。 皇帝坐拥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俯首帖耳,便是忠臣;若敢质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便是大逆不道。 哪怕皇帝昏聩无道,残民以逞,只要你毫无怨言地顺从,便是“忠臣孝子”,成了庙堂牌坊。 反之,纵使你心怀苍生,为民请命,只要不跪拜龙椅,便是乱臣贼子,活该千刀万剐,合该九族俱灭。 “君教臣死,臣不死不忠。”一个社会越是声嘶力竭标榜什么,那东西便越易被扭曲得不成模样。 普通人眼中的“奸”,往往是皇帝心里的“忠”——这悖论,是权力最赤裸的真相。 唐玄宗用李林甫,宋高宗用秦桧,嘉靖用严嵩,乾隆用和珅。皇帝用人,哪管他是否清廉?只问是否省心。 谁让他高枕无忧,谁便是股肱之臣;谁令他眉头紧锁,谁便是眼中之钉。奸臣的看家本领,无非“投其所好”。 李林甫,为玄宗挡下横征暴敛骂名,严嵩,替嘉靖压制清流文官的谏言,秦桧,给高宗背了杀害岳飞的铁锅,和珅,则为乾隆的奢靡搜刮财富。 为何帝王偏爱此辈?龙椅之下,白骨森森。 帝王最惧的,从非外寇铁蹄,而是权臣的逼宫。贪官不过窃财,权臣却是要命! 奸臣需帝王羽翼庇护,帝王需奸臣暗处效劳,彼此借力,同污合流。诚如古语所道:“伴君如伴虎”,而奸臣,恰是帝王爪牙最利的虎伥。 荀子:“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 忠奸之分,本不在行为表面光鲜与否,而在核心利益归属何方。奸者谋私利,忠者卫其主,义者系苍生,仁者存本心。 千年历史如迷雾,忠奸之辨,常如雾里看花。何故?胜者王侯败者寇,青史朱笔,从来由胜者挥毫。 立场不同,忠奸的标尺便天差地别。 帝王眼中的“奸”,是动摇其宝座之人;大臣口中的“奸”,是媚上压下之徒;百姓心里的“奸”,是鱼肉乡里之贼。 帝王所赞的“忠”,不如称其为“忠犬”——唯主人之命是从;大臣所守的“忠”,是忠于胸中道义,忠于天地良心;百姓所盼的“忠”,是清如水、明如镜,不徇私情。 千百年来,文天祥、关云长、岳飞焚香立庙,奉若神明;京戏台上,却将曹操、司马懿、赵高抹成惨白鬼脸。 忠耶?奸耶?俗语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拒牵于一己私利者,奸也;心系万家寒暖者,忠也。 知错而怙恶不悛者,奸也;闻过而改之如流者,忠也。因欲而戚戚汲汲者,奸也;由道而兢兢业业者,忠也。 真正的“忠”,既不盲忠君王,亦非死守国号,更非愚忠一事一物,而是忠于内心不灭的良知。 此心光明磊落,俯仰无愧,便是大忠。恰如刘震云点破世相:“江湖就是人,人就是江湖。” 世上本无纯粹的好歹,野蛮人彼此吞噬,文明人相互欺瞒。骗子待你“真心”,只因他真心要骗你。 千年风雨,人性进益微如尘埃。权力如巨兽,道德在它面前常如薄纸,唯有刚性的规则方能划定边界。 道德审判的喧嚣,剥开看,常常只是排除异己的利器。 人生在世,病痛之外,万千苦楚多由错谬的价值观滋生。迷茫、痛苦、内耗,常是被他人植入的意念所奴役。 龙椅之下,白骨如山,却都顶着“忠”或“奸”的谥号。历史账本,从不记录真实盈亏,只按赢家意志涂抹忠奸。当权者眼中忠臣,常是百姓心里豺狼。 所谓忠奸,不过权力舞台的面具。忠字背后,可能藏着帝王的“护院狗”;奸名之下,或立着黎民的“挡箭牌”。 真正的不朽,是穿透角色扮演,直抵人性深处那点不灭的微光——它不依附于任何冠冕名号,只在暗夜中独自灼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