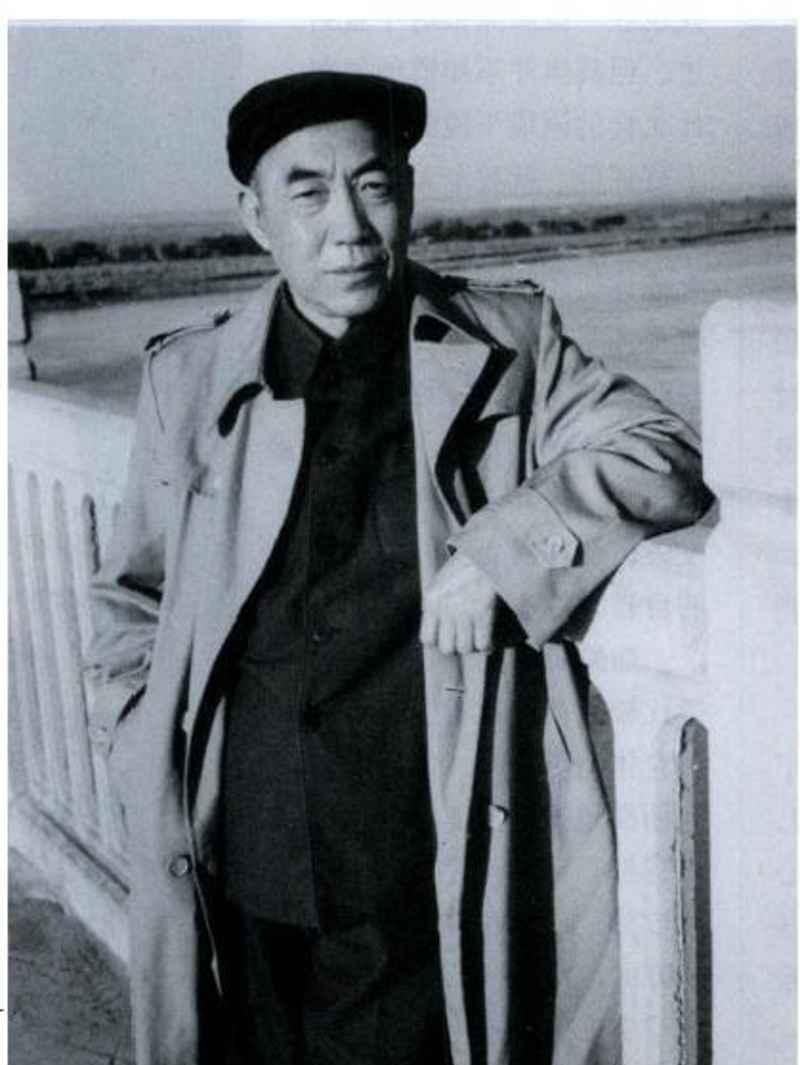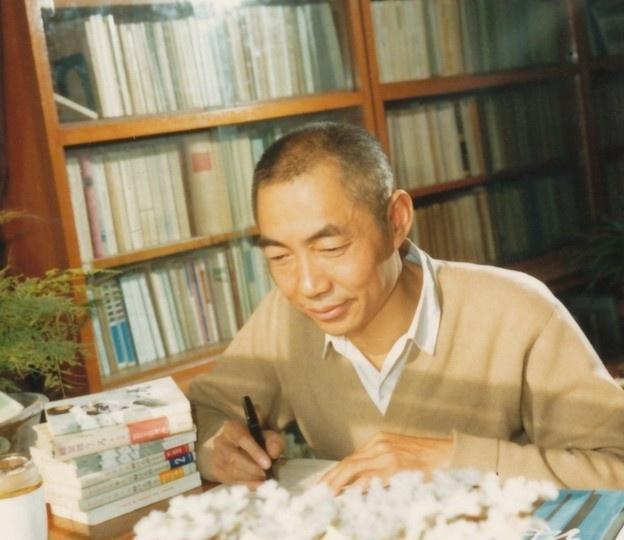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的变迁带来了文学评价标准与社会观念的巨大转变,浩然的作品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全新的审视与争议。尤其是在十年期间,当大多作家在时代的洪流中感到彷徨、苦闷,浩然却公开声称自己是 “幸福的生活和写作” ,这一言论如同一颗投入舆论漩涡的石子,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与热议。 在 1972 年 5 月发表的《幸福的生活和写作》一文中,浩然真挚地表达:“不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光辉指引,我这样一个年纪轻轻,政治思想还不成熟的写作者,岂不早被修正主义的黑风恶浪所吞没?我恨透了修正主义者,恨透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这种恨,更激起我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热爱和感激;因此我也就更加倍地感到:我们这一代的写作者,的确是幸福啊!” 国内多位学者批评浩然,而香港周刊却把《艳阳天》排进小说百强!陈侗在他的《为浩然辩护》中说,"对《艳阳天》的批评配不上《艳阳天》,电影《艳阳天》配不上小说《艳阳天》,就连对电影的批评也配不上电影,唯一配得上的可能是画家方增先为《艳阳天》画的插图。《艳阳天》如果不便跻身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之列,至少也是建国以来最值得被20世纪文学批评加以分析的一部作品。可惜的是,它的文学价值在当时被忽略和掩盖了。" 张德祥在《我所理解的浩然》中说,"应当承认,浩然所创造的那些农民形象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代表作《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虽然写于不同的时期,但一以贯之的是对于农民文化中那种传统人格精神——人要活得正直、正气乃至正义的追求","就农民形象创造的丰富性与丰满性而言,当代作家中很少有与浩然相匹的"。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星河里,浩然是一颗极为独特的星辰,他的创作生涯与作品承载着特定时代的深刻印记,在文学史上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浩然始终坚守 “写农民,给农民写” 的创作理念 ,将目光牢牢锁定在农村生活与农民形象上,创作了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作品,如《艳阳天》《金光大道》等。这些作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犹如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深受广大读者,尤其是农民读者的喜爱与追捧。 在这场激烈的争议风暴中,浩然的内心世界犹如一座被暴风雨侵袭的孤岛,充满了委屈与苦闷 。他始终认为自己的创作是真诚的,是对时代的真实反映,自己只是在尽一个作家的本分,用文字记录那个时代农民的生活和思想 。然而,外界铺天盖地的批评和质疑,让他感到自己的努力和付出被无情地否定,这种不被理解的痛苦如同一把尖锐的刀,刺痛着他的内心 。 从浩然与刘绍棠等人的交往故事中,我们能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他内心的这种挣扎。1979 年,在刘绍棠家中,蓝翎当着浩然的面不客气地表达了对浩然小说的看法 。蓝翎直言《艳阳天》虽然展现了浩然的看家本领,但《金光大道》却被他评价为 “没金光”,认为写一部即可;对于《西沙儿女》,蓝翎更是毫不留情地批评其散文不像散文,小说不像小说,人物形象也仿佛是京郊农民的生硬移植 。面对这些尖锐的批评,浩然的脸瞬间涨得通红,那是一种被当众否定后的窘迫与尴尬 。但他只是默默地听着,没有进行任何反驳或者辩解,他的沉默中,既有对他人意见的尊重,也包含着内心无法言说的委屈 。 刘绍棠在此时对浩然的理解和支持,显得尤为珍贵 。刘绍棠深知浩然的为人,他对浩然说:“浩然是个好人。如果换个人,处在他的地位,会比他做得好?我看未必。浩然没往上爬,不当官,没打小报告,没写效忠信 。” 刘绍棠的这番话,无疑是对浩然人格的高度认可,也让浩然在冰冷的质疑声中感受到了一丝温暖 。浩然感动地回应:“绍棠,我很感激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