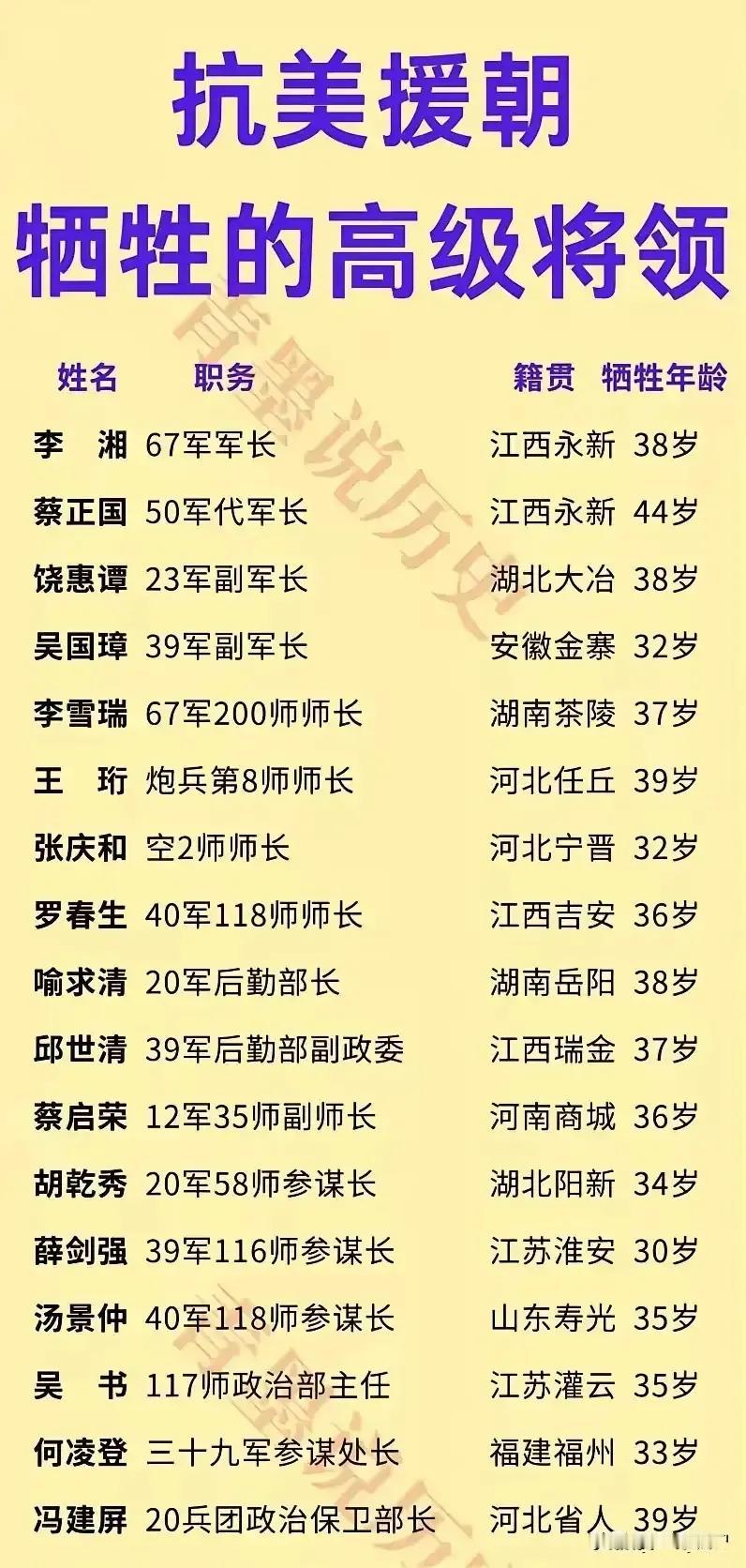1956年,李玉琴向溥仪提出离婚,多年后溥仪回忆:当年我对不起她 “1962年10月,北京饭店门口,我真能见到她吗?”溥仪压低嗓音,小心问身旁的工作人员。距离那份离婚判决生效已经五年,他仍然摸不透李玉琴此刻的心情。几分钟后,那个剪着短发、穿灰色呢子大衣的女子出现了,一如当年爽利,只是眼神里少了徘徊。 会面的寒暄不过十来句,两人都刻意避开“皇妃”“战犯”这类词。李玉琴只是淡淡地说:“你改造得不错。”溥仪点头,却突然想起1956年冬天她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那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里说出的那句——“离了吧,这样对谁都好”。当时他怔住,后来回忆起那一幕,总觉得自己开口太晚,挽留太轻。 把时间推回十三年前。1943年8月,伪满洲国宫内府忙着给傀儡皇帝续娶。日本顾问吉冈安直接连跑数家女校挑照片,六十多张一字摊开在溥仪面前。溥仪在排斥“日本侧室”的念头驱使下,选中了年仅十五岁的李玉琴——理由简单,年纪小、好掌控。李玉琴以为自己得了奖学金,进宫当天还追着太监问“教室在哪”。没人回答,她却从下一刻开始被贴上“福贵人”的身份标签。 被迫“册封”后,她的日常是唱京调、背家谱、等待皇帝召见。溥仪一面端着天子架子强调“三从四德”,一面又把自己囚徒般的处境和盘托出。李玉琴后来回忆:“我们像两个迷路的人,互相取暖,却都看不清出口。”短暂的温情并没化成稳固的感情,原因很现实——战争来了。 1945年8月,苏联红军逼近长春,日本人指挥溥仪西逃。只有三架飞机,名单里没有李玉琴。她站在空场上看着螺旋桨卷起尘土,飞机越升越高,最后化作黑点。那一刻,年仅十七岁的她第一次真正理解“弃子”二字。之后,李玉琴随伪满残部被八路军收编,先到通化,再到长春。八路军干部告诉她:“旧皇妃也得有新身份,你考虑离婚吧。”她摇头,“好女不嫁二夫”,一口气撑了十年。 1955年春,一封来自抚顺的信打破僵局——寄信人是溥仪。信里先谈认罪,再谈思念,“亲爱的玉琴”几个字把她拉回过去。她带着变卖首饰换来的车票去了抚顺。第一次会见,溥仪关心的是自己能否活着出狱;第二次会见,他仍旧纠结刑期;第三次,她明白眼前的男人与其说需要妻子,不如说需要一个“听众”。李玉琴开始动摇:“改造要紧,你我都还年轻,各自活法吧。” 1956年12月,气温零下二十度,她第五次去抚顺。简单寒暄后,李玉琴直截了当:“岁数相差悬殊,你在高墙里,我在外面,人前人后都不自在。过不去的坎就别过了。”溥仪愣住,过了好一会儿才吐出一句:“如果这是你想要的,我签字。”他后来在自传里写:“那天我没掉泪,是因为心里空了;我亏欠她的,不止一个道歉。” 1957年4月,抚顺市河北区人民法院判决准予离婚。李玉琴拿到判决书时,天正下雪,她在院门口站了几分钟就把文件折好放进包里,然后搭车回长春图书馆上班。日子往前走,新工作、新同事、新家庭都来了。1960年,她与吉林广播电视台工程师黄毓庚登记,次年得子。有人背后议论:“前皇妃再嫁,真不怕流言?”李玉琴只回一句:“我怕的东西早在飞机起飞那天见识过,剩下的没什么可怕。” 另一边,溥仪在抚顺继续学习、劳动、写检查。1959年特赦前夕,他对管教员说:“如果能出去,我想见李玉琴,跟她好好说声对不起。”真正见面已是1962年政协文史小组会议。短暂叙旧后,两人各自归位:他是北京市园林局特种园艺师,她是长春市政协委员。往后几十年,偶有活动相遇,客客气气,像同事,多说一句都是额外。 1975年,溥仪病逝。报纸登出讣告那天,李玉琴正在图书馆整理期刊。同行悄悄递来报纸,她停了几秒,说:“走了也好,他总算心安。”没再表态,转身继续工作。日子依旧按部就班:审书目、写提案、下基层查物价……2001年春,她在病榻上嘱咐子女:“我最看重的不是‘福贵人’,也不是离婚,而是后来有机会做点实事。别替我写回忆录,活人搞好眼前的活儿更要紧。” 李玉琴的一生横跨帝制余晖、伪满黑暗、战后重建、新中国草创。从被选妃那天起,她就像被历史推着走;1956年那纸离婚判决,是她第一次用自己的手调转方向。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写下那句“当年我对不起她”,算是迟到的注解。可若论人生得失,李玉琴后来常对亲近的年轻同事说:“人得靠自己,别指望谁给你盖章幸福。”说这话时,她的眼神平静,没有哀怨,也没有炫耀,倒像多年馆藏书页上的一行批注——不鲜亮,却耐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