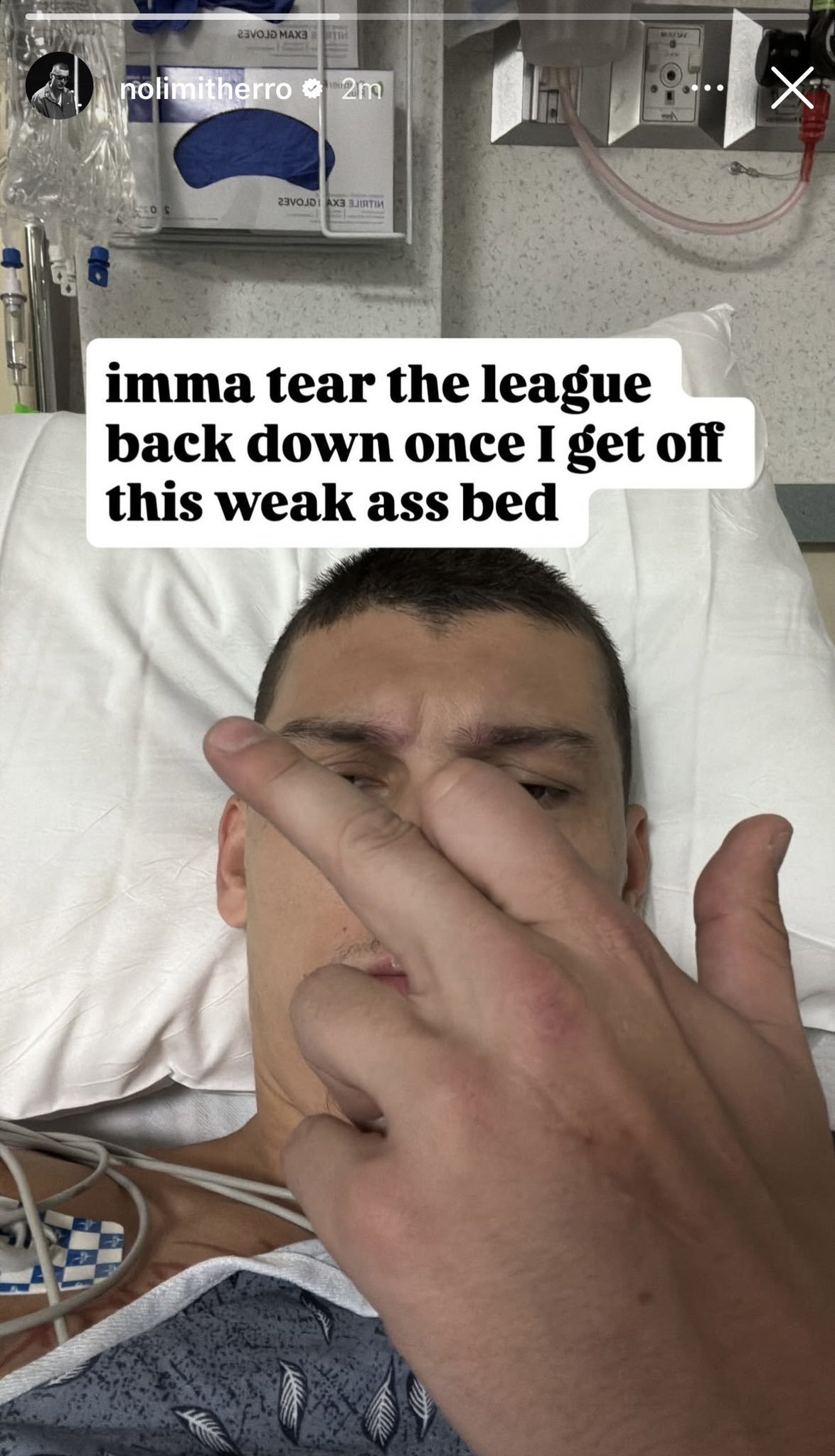1952年大凉山深处,解放军从奴隶主手里救出一个眼睛都快烂掉的汉人。当兵的看他太遭罪了,就问:你叫啥名?他费老大劲才挤出三个字:“帅士高”。 1935年5月,安顺场。大渡河的水,那叫一个凶。红军被堵在了河边,前头是咆哮的河水,对岸是国民党早就架好的机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河面。后头呢?追兵的马蹄声,感觉已经能震得地皮发麻。当年太平天国的石达开,就是在这儿,全军覆没。这地方,是个死地。 想活命,就得过河。怎么过?唯一的路,就是靠船。 可船在哪?国民党兵早就把河边的船搜刮干净,剩下的,船工们也藏得严严实实。 帅士高,当时才17岁,是河边水性最好的小伙子。国民党兵抢他家的粮食,抢他家的船,他早就憋了一肚子火。红军找到他,说咱们是给穷人打天下的队伍,要过河去打那些欺负老百姓的坏蛋。 帅士高二话不说,把藏在芦苇荡里的最后一条小木船拖了出来。 那天晚上,月亮都被乌云遮得严严实实。帅士高和另外十六个船工,成了红军的“特种部队”。 “开船!”一声令下,小船像箭一样射进漆黑的河心。 刚到河中央,对岸的火舌就喷了出来。子弹“嗖嗖”地贴着头皮飞,打在船板上,“噗噗”作响,溅起的水花冰凉刺骨。有个船工肩膀上中了一枪,血一下子就把半边身子染红了,可他咬着牙,手里的船篙愣是没停。 帅士高站在船头,光着膀子,一身的腱子肉在风里绷得像石头。他脑子里就一个念头:快点,再快点,多送一个过去,就多一分希望。 一趟,两趟,三趟……来来回回整整十七趟。 最后一次靠岸,他手里的竹篙都磨秃噜皮了,虎口裂开,血顺着胳膊往下流。他整个人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分不清是河水还是汗水。 一个红军干部往他手里塞了几块银元,他想都没想,一把推了回去,嗓子都喊哑了:“等你们打赢了,回来给我修条安稳的道,比啥都强!” 红军走了,国民党的报复也来了。 他们找不到红军,就把气撒在这些船工身上。帅士高的家被一把火烧成了灰,他爹妈被打得半死。他只能往大凉山深处跑,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可他没跑出国民党的手掌心,却掉进了另一个地狱——被当地的奴隶主给抓了。 在那十七年里,“帅士高”这个名字没人再提。他成了一个没有名字的“娃子”,一个会喘气的牲口。 白天,他被铁链锁着去凿石头。山里的石头硬得像铁,一锤子下去,震得膀子发麻,溅起的石屑崩进眼睛里,又疼又痒。他想用手揉,奴隶主的皮鞭就抽过来了,骂骂咧咧:“干活还偷懒,想死啊!” 晚上,他就睡在牛棚里,跟牛睡在一起。吃的呢?就是奴隶主吃剩下的,有时候是一块发霉的馍馍,有时候是一碗馊了的野菜汤。 他的眼睛,就是在那时候慢慢坏掉的。先是被石屑弄伤,后来又被牛棚里终年不散的烟火熏,慢慢地,视线开始模糊,最后,就只剩下一片黑暗和钻心的疼。 他不是没想过跑。有一次,他趁着看守打盹,挣脱了链子往山下跑。可没跑多远,就被抓了回来。奴隶主用烧红的烙铁烫他的腿,那种皮肉烧焦的味道,他一辈子都忘不了。 从那以后,他好像认命了。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偷偷摸索着,在牛棚的泥地上划拉。划什么?划一条河,划一条船。他一遍遍地回想那个晚上,回想那些年轻的、带着笑的红军战士的脸。 那十七趟渡河,成了他黑暗世界里唯一的光。 1952年,当解放军战士把他从牛棚里抬出来的时候,他已经瘦得脱了相。军医给他清洗眼睛的伤口,脓水和血水混在一起,旁边的年轻卫生员都看吐了。 在部队的营地里,他慢慢缓了过来。有人喂他喝了半碗热腾腾的小米粥,那是他十七年来吃过的最香的东西。 他看不见,就用手到处摸,摸到战士们穿的军装,摸到他们手里的钢枪,嘴里不停地念叨:“红军……是红军回来了吗?” 战士们告诉他:“老乡,现在不叫红军了,叫解放军。新中国都成立三年了!” 听到“新中国成立了”这几个字,这个被折磨了十七年的汉子,突然一把抓住军医的胳膊,那干枯的手像铁钳一样有力。他那两个烂掉的眼洞里,涌出了浑浊的泪水。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们能成事!”他哭得像个孩子。 后来,中央派了专人来看望他,问他有什么愿望。所有人都以为他会要钱,要个官当当。可他沉默了很久,只提了一个要求:“我想回大渡河,再看看。” 1953年,他的眼睛经过治疗,有了一点点微弱的光感。部队派人陪着他,回到了那个让他魂牵梦萦的安顺场。 河还是那条河,但水声好像没有那么响了。河上,一座崭新的大桥飞跨两岸。 他被人扶着,一步一步走到桥中央。他伸出布满老茧的手,摸着冰凉的桥栏杆,脚在桥面上使劲踩了踩,咧开嘴笑了。 “结实!”他说,“要是当年有这座桥,咱们的战士,就不用拿命去填了。”风呼呼地从河面吹过,吹动着他的衣角。那一刻,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