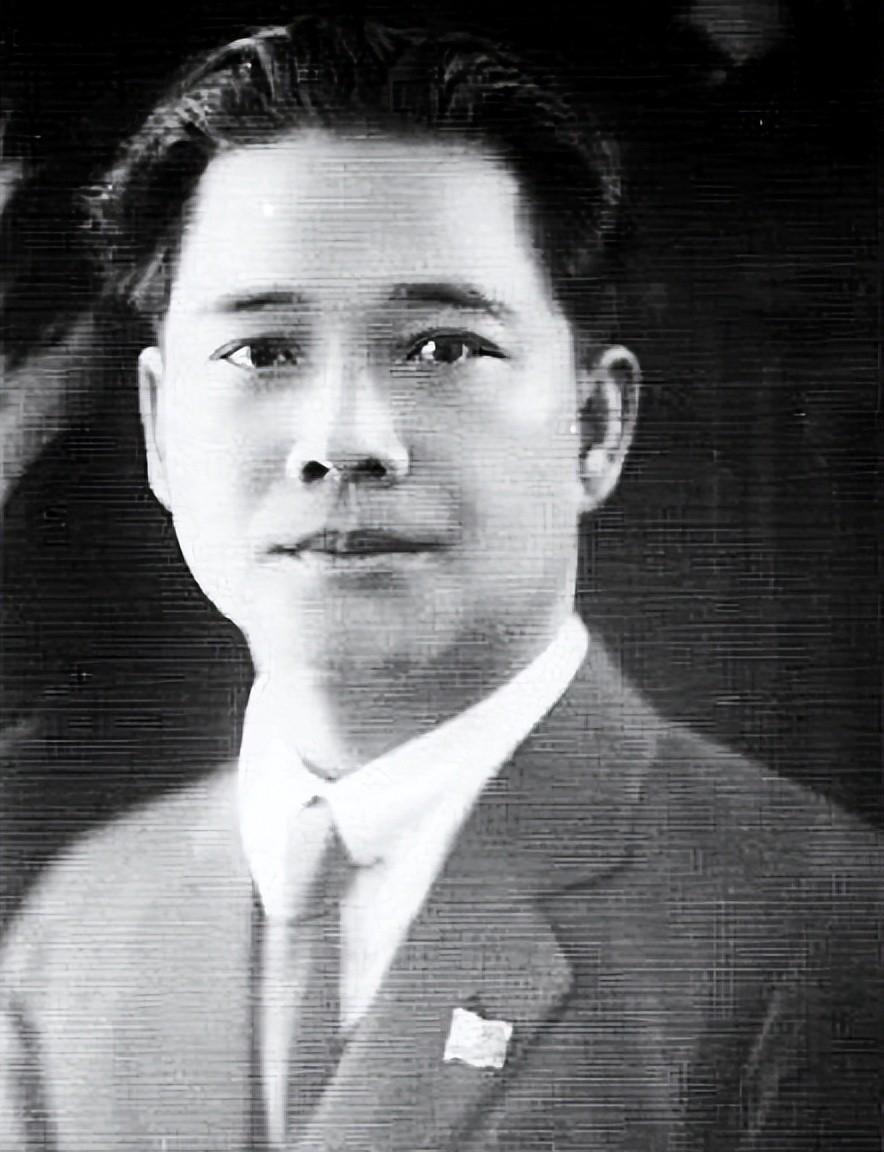1959年汪精卫之妻病逝,临终前叮嘱儿女:不能忘记报答国家的恩情 1959年6月17日凌晨四点,上海提篮桥监狱医院的灯一直亮着。值班护士俯下身时,听见病床上的老人用极低的声音重复一句话:“不要忘了国家,对国家一定要报恩。”说这话的,正是曾在南京雨花台上风光一时的“第一夫人”——陈璧君。她的生命走到尽头,留下的却是一个跌宕半世纪的政治坐标。 追溯到1891年,陈璧君出生在马六甲一个富商家庭。富裕让她早早接触西式教育,也让她厌倦殖民地的空气。16岁那年,她在广州听孙中山演讲,被“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字点燃,直接递上加入同盟会的申请表。同行的闺蜜愕然,她却一句“革命也要抢先”扔下,旋风般卷进粤港的地下网络。 辛亥风云散去后,1912年农历腊月,她和汪精卫在北京成婚。那是一场轰动的“革命婚礼”。朋友们调侃:“你俩名字加一起正好是‘精卫填海’。”陈璧君笑着拍桌:“那就一起填。”彼时两人接连为孙中山奔走,极力推销共和理念,在报纸专栏写文章,在学校礼堂做演讲,风头无两。 转折出现在1925年。孙中山病逝之前,临时授意汪精卫主持党务。然而蒋介石凭军校与北伐声望急速上升,刚从欧洲归来的陈璧君一踏上海滩,就明显感觉到社会焦点移向宋美龄。“蒋夫人能有的,我也要有。”她在晚宴上对汪精卫说的这句话,成为后来史家判断其价值观巨变的关键节点。 1938年冬天,东京特务机关加紧对南京、上海的渗透。日本人抛出“华中自治”诱饵,陈璧君急于借机再上权力巅峰,一再催促汪精卫南下与日方接触。传言中那句刺耳的“难道连卖国都要排在老蒋后面?”虽无档案佐证,却与她当时的言行十分契合。1940年3月,南京汪伪政府挂牌,她公开戴上“主席夫人”的徽章,意气风发。 好景只维持四年。1944年11月,汪精卫在名古屋大本营病逝,陈璧君孤身回国。日本败象明显,各地抗日力量步步紧逼。1945年9月,郑介民化名“蒋秘书”发出一封请柬,把她从上海骗到昆山路口。一辆黑色雪佛兰门一关,她已成阶下囚。押送重庆途中,陈璧君冷笑一句:“我怕死?不,我只厌烦无穷的牢狱。” 国民政府对她提起汉奸公诉,庭审僵持不下。她抓住蒋介石曾与日方私下接触的小道消息,反咬一口,把法庭弄得尴尬。1949年春,解放军南下,国民党撤往台湾,陈璧君被移交人民政府,转押上海。彼时宋美龄寄来书信,为其求情。中央批示:可考虑特赦,但须本人彻底认罪。结果她在纸上写了近两万字“自传”,一句检讨也没有,只冷冷写下“我无罪”。 面对如此顽固,被管理部门归为“重点教育对象”。监狱安排她每日阅读人民日报、苏州河边工人夜校的教材,还特许她收听半小时新闻广播。1952年一次急腹症手术中,主刀医生使用了刚进口不久的青霉素。术后有人问她感觉,她只回一句:“共产党比我想的周到。”态度微妙起变化。 1954年深秋,她提交第一份思想汇报,字里行间首次出现“错误”“责任”字样。监管干部没急着表扬,反而在次日例会上提出:“继续观察,不搞形式主义。”这种缓慢而坚实的心理渗透,比任何强迫口号更有力量。随后的三年,陈璧君再未对监管工作提出额外要求,偶尔甚至主动帮医护人员搬药箱。 1959年春,她的肾衰竭加重。六月初,医生告知病危。她要求把儿女叫来,实际只来了小女儿汪文仪。病房里,母女低语:“妈,您还有什么要交代?”陈璧君抬手示意靠近:“国家待我不薄,记住这句话。”简短四十字遗嘱,除了感谢医疗照顾,只剩一句核心——“不能忘记报答国家的恩情。” 6月17日清晨,心电监护仪线条归零。监狱方面按照规定通知家属,并为其备棺下葬。遗体没有声势浩大的送行,只有三盆白菊。新华社一则不足百字的消息,对外公布她的死亡时间和病因,未加评语。彼时的共和国正忙于十年规划,无暇对一个曾经的女汉奸发出更多浪花。 值得一提的是,她的子女后来陆续回到大陆工作。其中长子汪兆铭执意参加援藏工程,直到1970年代仍在高原线上奔走。在采访里,他只用八个字回顾母亲的遗愿:“知恩图报,自当尽力。” 陈璧君的一生,前半段追随革命,后来却随权力沉沦,结果在铁窗与病床上看见另一种答案。她临终那句“报答国家”的嘱托,并不能洗刷罪行,却昭示了一个事实:新中国对待历史遗留人物,选择的是改造而非简单清算。这一点,或许比任何惩罚都更能撼动曾经的“第一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