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前往灵光寺上香,被前来游玩的八旗子弟拦着清场,康熙开口问:可知我身份?那子弟却狂喊:管你是谁,快跪下!灵光寺,京郊名刹,素以香火鼎盛、古木参天闻名。 1684年,京郊灵光寺的古银杏正落得金黄。 谁也没料到,这日来上香的年轻皇帝,会因几个八旗子弟的撒野,揭开大清王朝最隐秘的疮疤。 这年入秋,直隶总督的密折像根细针,扎在康熙心头。 折子上写着,京郊八旗子弟结党横行,强占民田、辱骂百姓,地方官因“旗籍”二字束手无策。 康熙放下朱笔,盯着案头摊开的《八旗户籍册》,看着那些世袭的勋贵姓氏,若有所思。 当年跟着太祖太宗开疆拓土的勇士之后,如今竟成了民间的活阎王。 第二日,他换了身粗布青衫,带着张武等几个侍卫,悄然进了灵光寺。 这座以千年古刹闻名的寺院,此刻正被一群穿绸裹缎的八旗子弟搅得鸡飞狗跳。 领头的是个二十来岁的青年,石青马褂上绣着暗纹,腰间羊脂玉坠晃得人眼晕,发间的赤金冠昭示着勋贵出身。 他挥着马鞭驱赶香客,连供桌上的香烛都踢翻了几个。 嘴里还嘟嚷着:“爷们儿要清场祈福,哪个不长眼的敢拦?” 香客们缩着脖子往后退,有位白发老太太被撞得跌坐在地,线香撒了一地,烫了手也不敢捡,只敢盯着那青年的靴底发抖。 张武的手早按在腰刀吞口上,指节捏得发白。 只要康熙一个眼神,他能把这伙人按在地上。 可康熙抬手拦住了他,因为他早已清晰的看到了那青年腰间的玉坠、靴底的云纹。 他心里有数这,是哪家世袭勋贵的崽子,从小到大没吃过苦的主儿。 那青年见康熙不过是个穿旧衣的老头,更嚣张了。 他甩着马鞭走到康熙跟前,鞭梢几乎扫到老人胡须:“老东西,聋了?爷叫你跪下!” 说着就要推搡。 一旁的张武,刀几乎要出鞘,康熙却稳稳站着。 “你祖父随太宗打松锦时,可曾教过你‘畏法度、惜民力’?” 青年愣了愣,随即梗着脖子笑:“少拿陈谷子烂芝麻唬人!如今这天下,是爷们的天下!” 康熙不再多言,朝张武使了个眼色。 张武从怀里掏出鎏金令牌,“啪”地拍在石桌上。 “康熙御赐侍卫令牌”八个字在阳光下刺目。 青年吓得脸色骤白,腿一软差点跪下,结结巴巴喊“您,您是?” 直到此时,被驱赶的香客才敢抬头。 有人认出令牌,扑通跪下来喊“皇上圣明”。 康熙却没理他,转身对香客们说:“都散了吧,今日之事,朕给你们个交代。” 回宫的路上,康熙没发一言。 他不是没动过怒。 这青年若在民间,早该被杖毙,可杀一个容易,治一窝难。 夜里,他翻出直隶总督的密折,又让人查了那青年的底细。 祖父是开国二等功臣,父亲袭爵后便撂了挑子,家产倒腾、欺压百姓是常事,连朝廷拨给八旗的粮饷都敢私吞。 三日后,三道圣旨从紫禁城发出。 其一,八旗子弟须学武艺、务农桑,游手好闲者停发粮饷。 其二,地方官若因“旗籍”包庇罪犯,同罪论处。 其三,派钦差彻查京郊旗人田产,强占的必须归还百姓。 灵光寺的和尚后来常说,那年秋后的风里,飘着股不一样的味儿。 不是香火,是铁腕。 百姓们渐渐敢抬头走路了,茶馆里议论的不再是“惹不起旗人”,而是“听说了吗?县太爷把占田的王公子抓了!” 当然,这事没那么简单。 那青年的父亲闹到宗人府,哭着喊着“祖宗脸面何存”。 有些旗人老爷聚在茶楼骂“皇上动了咱们的铁杆庄稼”。 可康熙没松口。 因为,他在等,等这些“蛀虫”明白,大清的根基不在旗籍册上,而在田埂间的犁铧里,在市井中的烟火中。 三年后,直隶巡抚的奏报里多了句话:“今岁秋税,旗民同役,田亩无争,百姓称快。” 康熙合上奏折,望着窗外的梧桐叶,想起灵光寺那日飘落的银杏。 他知道,改革像这秋风,吹落的是枯叶,长出来的是新枝。 有人说,康熙那日若亮明身份,一刀杀了那青年,不过是桩宫廷轶事。 可他偏要忍,偏要查,偏要把“八旗积弊”这根毒刺连根拔起。 因为他穿的不是龙袍,是百姓的粗布衫。 他看的不是奏折上的字,是人间的泪与血。 主要信源:(百度百科——清朝八旗子弟有多狂?百姓不敢惹官府不愿管,连皇帝都无可奈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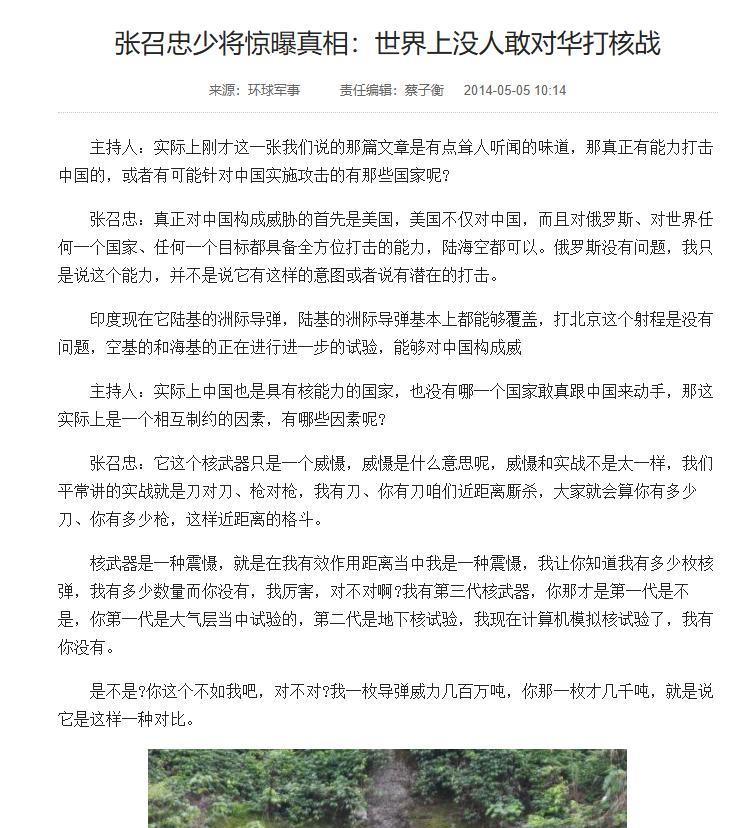






用户84xxx55
扯淡
奇奇怪怪
我草,还有人洗
用户16xxx01
呵呵
用户10xxx22
令人最恶心的电视剧康熙私访记
123456
治国之道
伴花眠
大兴文字狱的是谁?
用户10xxx29
1684年,康熙才三十多。
a stranger
前面说来上香的年轻皇帝,后面说穿旧衣的老头,穿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