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提到继母朱枫,85岁的阿菊声音依旧冷硬:“我不想再提她。”一句话,让人心头一紧。 朱枫,原名朱贻荫,是她继母。可要是你去问阿菊,她从没承认过这层关系。 可问题来了,为什么一个女人,到了八十多岁,连一句“她是我继母”都不肯承认? 事情还得从头说。 1950年夏天,台北马场町刑场,朱枫身中七枪,当场牺牲。 她死时,没留下遗言,没穿囚衣,穿的是一件干净的旗袍,嘴唇咬得紧紧的,身边还有吴石、聂曦等人。 这一年,她刚满45岁。 但在台北另一头的巷子里,15岁的阿菊正被祖母推着躲在屋里,关掉收音机、关上窗户,不许出门。 没人告诉她发生了什么,只是那晚,她听见祖母在屋里哭了一整晚。 她听得懂,但不敢问。她知道,那是“她”的事。 那时候,朱枫已经不是那个温温柔柔、会陪她绣花、讲故事的女人了。 她成了“通匪叛徒”。可在更早些年,她不是这样的。 1938年,在镇海,朱枫开了一个义卖展,展台上全是她自己做的刺绣、雕刻、金石作品。 人来人往,她一分钱不留,全捐了出去。 “为前线将士出一份力。”她说话从来不大声,但有种让人不敢反驳的底气。 那时她还没再婚,还只是个带着女儿独自生活的寡妇。 朱晓枫,就是她的亲生女儿。 阿菊不是。阿菊是朱枫第二任丈夫朱晓光的女儿。 婚后,她照顾阿菊,也管教她。阿菊小时候脾气倔,朱枫从不骂她一句,但也从不哄。 “你要争气。”朱枫说,“以后没人会因为你哭了就让你活下去。” 那时候阿菊不懂,只觉得这个女人冷冷的,像从不笑。 可她也记得,有一回家里断粮了,朱枫把祖传的钻戒拿去卖了,还骗她说是自己在上海的朋友送了点米回来。 她不傻,知道那是假的,但她没拆穿。 再后来,朱枫去了重庆。 1943年,她在“珠江食品店”做“堂倌”,其实是在送情报。她从不多说话,工作勤快,谁也没想到她是地下党。 有人说她被打过,被关过。也有人说她咬牙吞金,差点死在牢里。但这些事,阿菊从没听她说过。 她只记得朱枫回家那次,背上有一块疤,是裂开的皮肉重新长合的样子。朱枫说,是摔了一跤。 阿菊信了。 可很快事情就变了。 1949年底,朱枫以“探亲”为名去了台湾。 谁也不知道她是去送情报的。她见了吴石,见了蔡孝乾,传过图纸、交过胶卷。 她做事一丝不苟,连信封上的字迹都换了三种字体防追查。 但她没想到,蔡孝乾叛变了。 1950年2月18日,朱枫在舟山被捕,被押回台北。 她没哭,也没求饶。 在定海看守所,她吞下的是金锁片和金手镯,被抢救回来后,仍拒绝开口。 直到6月10日,她被枪决。 那天,阿菊正准备考试,邻居家的孩子跑来告诉她,“你妈被抓了。” 她没吭声。 晚上,祖母把她拉到灶房,递给她一张纸,上面写着“朱谌之”。她不懂这个名字。 祖母只说了一句:“以后,这人你不认识。” 从那以后,朱枫在阿菊的生命里,就像被抹去了。 可几十年后,朱晓枫找上门了。 2005年,她来台湾,找到阿菊。 “我是朱晓枫。”她说。 阿菊没说话。 “朱枫是我妈。” 这句话,像一把钝刀,慢慢割进阿菊的心口。 她没哭,也没认。 她说:“过去的事,别提了。” 朱晓枫递给她一张照片,是母亲就义前的黑白照,眼神坚毅,嘴角紧闭。 “你不想知道她最后的样子吗?”朱晓枫问。 阿菊摇头。 “我怕记起来。” 其实她早就记得了。 朱枫走后,她收拾衣柜时,发现了一包银元,和一封没寄出的信,信里说:“阿菊若听话,将来让她读书,不要靠人过活。” 她没告诉任何人,把信烧了,银元交给了学校换学费。 她不想欠她什么。 2010年,朱枫的骨灰找到了。 在台北富德公墓,编号77。 因为名字被误录为“湛文”,所以一直没人认领。 朱晓枫带人来确认,最后由台湾友人刘添财护送回大陆。 2011年,朱枫安葬在宁波镇海烈士陵园。 那天,阿菊没去。 她只是一个人在家,把那张母女合影从抽屉里拿出来,看了一会儿,又放回去。 “她从没叫过我一声女儿。”阿菊说。 “可我知道,她不是坏人。” 说完这句,她闭上眼,靠在椅背上,整个人像是松了一口气。 她说,“我不想再提她。” 可其实,提不提,心里都记得。 朱枫的牺牲,是信仰的选择。阿菊的沉默,是时代的代价。 她们,一个选择了牺牲,一个选择了遗忘。 可历史没忘。 她们的名字,都被写进了时间的背面,也写进了,那个谁也不敢说出口的年代。 信息来源:《沉默的荣耀》热播背后:台湾媒体人与朱枫的“追寻故事”——中国新闻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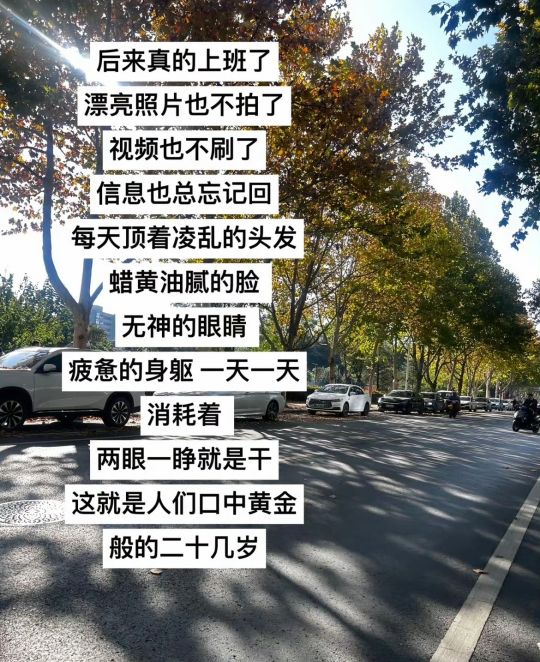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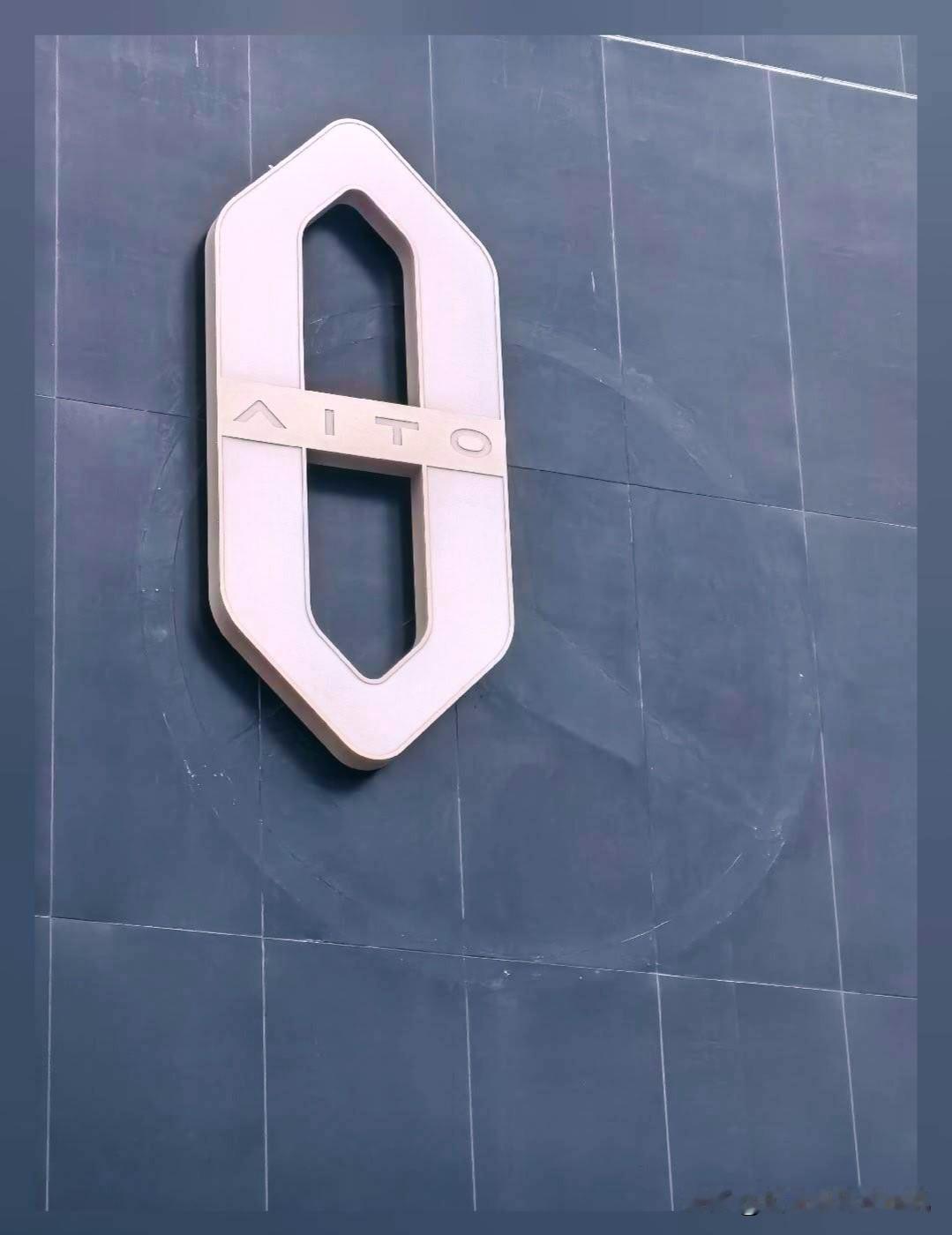

用户73xxx70
他们的牺牲,值得被永远铭记! 怀念先烈们,致敬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