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华人表示,华人精英移民到美国之后,不出两代,基本上都成为普通人 在硅谷的某栋玻璃幕墙写字楼里,一位戴着黑框眼镜的华人中年工程师正一行一行地敲着代码。 他叫陈立,47岁,斯坦福硕士毕业,曾在雅虎、亚马逊、Meta都干过,履历干净得像算法一样精准。 他的工位上摆着一张儿子的毕业照,背景是哈佛大学的草坪,阳光明媚,儿子笑得灿烂。 可那笑容背后,藏着一个在无数华人家庭中反复上演的剧本:一代精英的光环,到了下一代,慢慢变淡,再到第三代,可能就什么都不剩了。 “在美国,华人精英家庭的光环,大多撑不过两代。” 这是很多移民家庭心照不宣的现实。 陈立的父亲是上世纪80年代初第一批出国的访问学者之一,那时他们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园附近的学生宿舍,一家三口挤在一间不到20平的小屋里。 父亲白天做实验,晚上打两份工,母亲给中餐馆包饺子。 他们咬牙坚持,是为了让孩子接受这里“最好的教育”,他们确实做到了,陈立高中毕业时SAT成绩满分,进入斯坦福计算机系,一路绿卡、工作、购房、成家。 这是第一代移民的典型路线:顶尖学历、技术岗、勤奋型成功。 他们靠智力和努力在没有资源的情况下,硬生生地打开一条路,但他们也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所有希望压在下一代身上。 问题就出在这“希望”上。 陈立的儿子Jason的确没让他们失望:从小就是学区的优等生,进了哈佛读经济,实习做过投行,但毕业后,却选择了开一家咖啡店,地点在波士顿南区,主打“亚洲风味拿铁”。 父亲陈立第一次听到这个决定时,半天没说话,只是盯着那杯他尝不出味道的“抹茶燕麦拿铁”,像是在盯着一个失控的未来。 这不是个例。 在2022年的一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中发现,在美国出生的华人第二代中,选择继续从事工程、科学、技术等“父辈路径”的比例不足15%。 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比例接近45%,变化的背后,是文化和价值观的彻底转向。 第一代移民是“生存型”思维,认为一切都靠拼搏来换;第二代在美国土生土长,更多地把“成功”定义为自由、平衡、兴趣,“做自己”成了信条。 有不少华人二代在公开分享“逃出父母规划的生活”——他们不再执着于财务自由,而是情绪自由、身份自由。 也不能简单地说是“叛逆”或者“不上进”。 Jason的咖啡馆经营得其实不错,雇了5个员工,每月营业额稳定增长,他不是不努力,只是努力的方向和方式变了。 这是不是陈立那一代人心中的“成功”?他们拼命想复制的那个精英模型,似乎在现实中,越来越难传下去。 更深的原因,是一种叫“玻璃天花板”的东西。 在硅谷,华人工程师的比例超过20%,但在VP(副总裁)以上的高管里,华人占比不到3%。 技术再强,代码写得再漂亮,到了管理层,拼的是沟通、交际、战略判断、影响力——这些恰恰是传统华人教育里最缺乏的部分。 很多人在公司里干了十几年,职位停留在“高级工程师”,每天“干活不出错”,但也“看不到未来”。 陈立在Meta干了7年,一直没能升到Director(总监),他曾在一次内部反馈中听到这样的评价:“技术好,但领导力不够突出。” 类似的故事不胜枚举,很多人干脆不再往上爬,转而鼓励孩子“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问题是,“做喜欢的事”并不一定能延续家族的社会地位,到了第三代,情况更复杂。 很多华人家庭的第三代,中文已经不会说,春节也不过,甚至在学校选择填族裔信息时,直接勾选“Other”或“不愿透露”。 他们觉得自己是“美国人”,但又经常被提醒“你长得不像”。 有研究统计,在2020年之后,超过30%的亚裔美国青少年在校园中经历过种族歧视或身份质疑,疫情期间的反亚情绪更是加剧了这种“身份撕裂感”。 有个真实的例子——一位在纽约长大的华裔女孩,在大学选修中文课时写下这样一句话:“我不知道我是谁。我看起来像中国人,但我连奶奶讲的故事都听不懂。” 这不是她一个人的困惑,而是整个群体在文化传承上的断裂。 更多的家庭在代际转换中逐渐边缘化,走向“平凡”,但“平凡”就一定是失败吗? 近年来,一股“回流”趋势正在悄然发生,根据2023年中国人力资源研究院的数据,选择回国发展的北美华人专业人士比上一年增长了37%。 他们中不少是在美国职场受限、文化认同受挫后,开始重新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 代际断裂,不只是因为文化稀释,而是社会结构的限制与认同感的迷失共同作用的结果。 华人精英家庭的光环,为何难以传过两代?核心或许不是“能力断层”,而是“认同失焦”。 第一代人靠努力拼出了“社会资本”,第二代人拿着这份资本探索“自我价值”,第三代,可能连这份资本的语言和文化都不再理解。 这是一个族群在迁徙与融合过程中的必然代价。 信息来源:美华人第二代与父母渐行渐远?华人父母述不同境遇 2021-12-14 ·海外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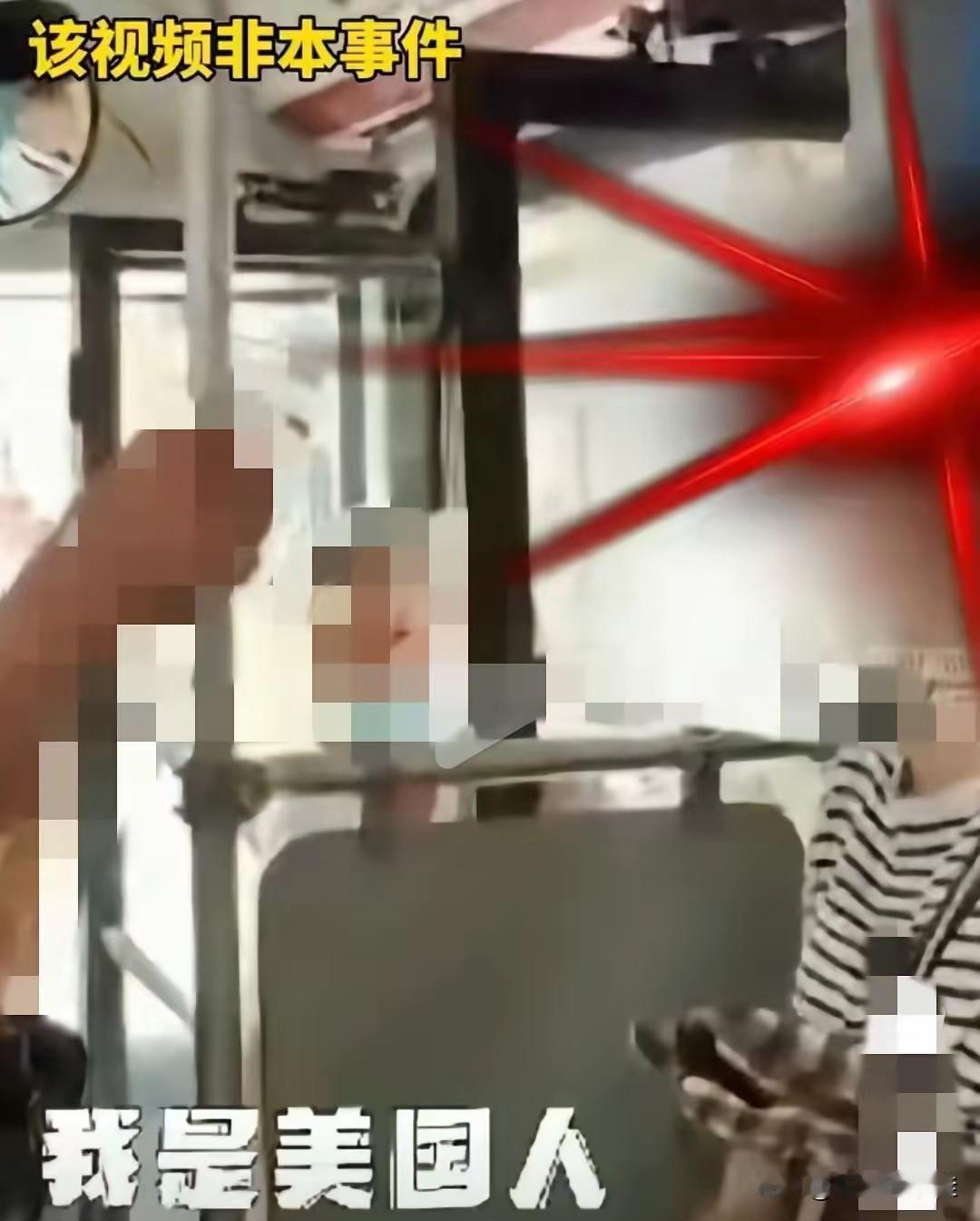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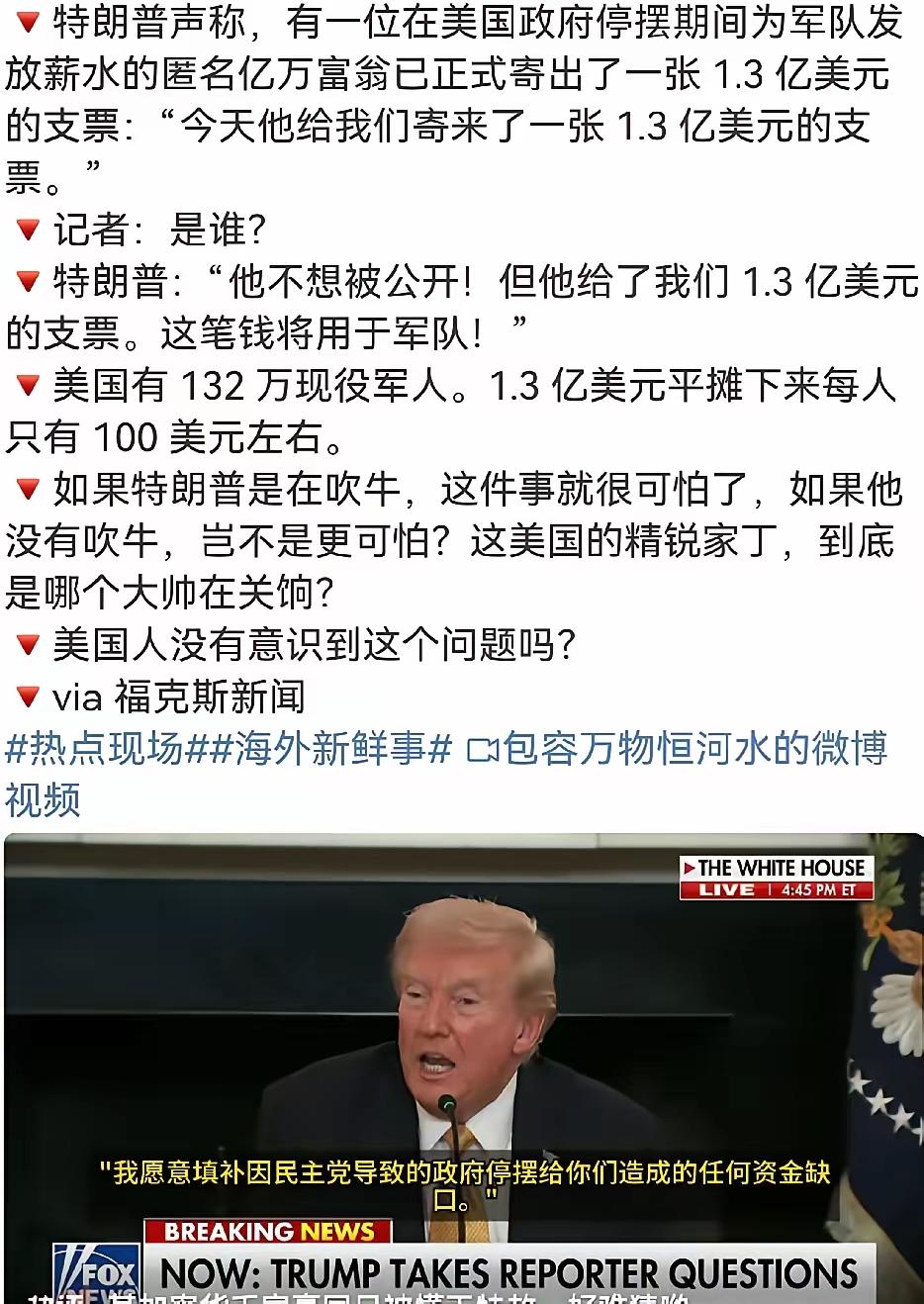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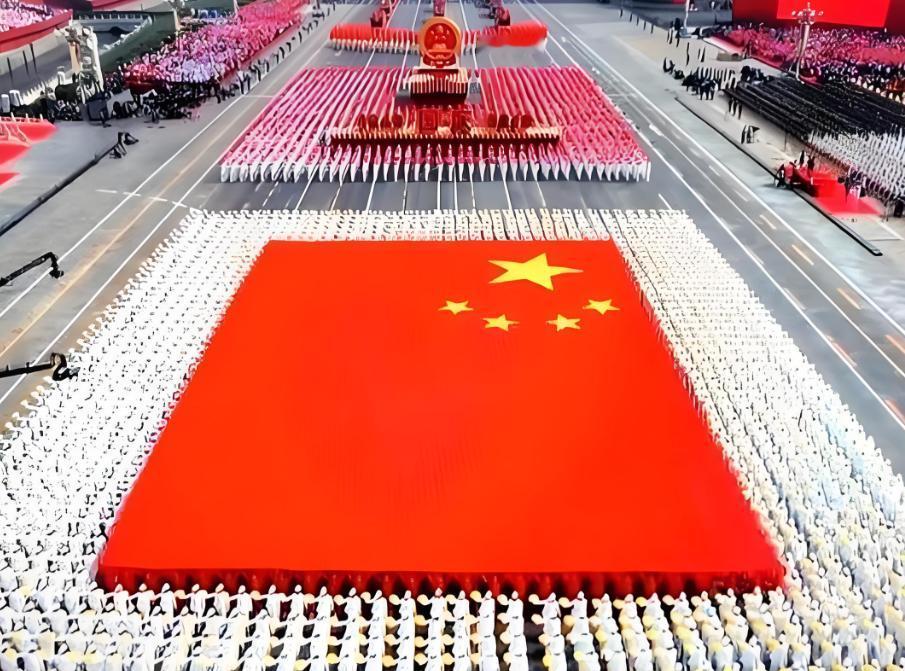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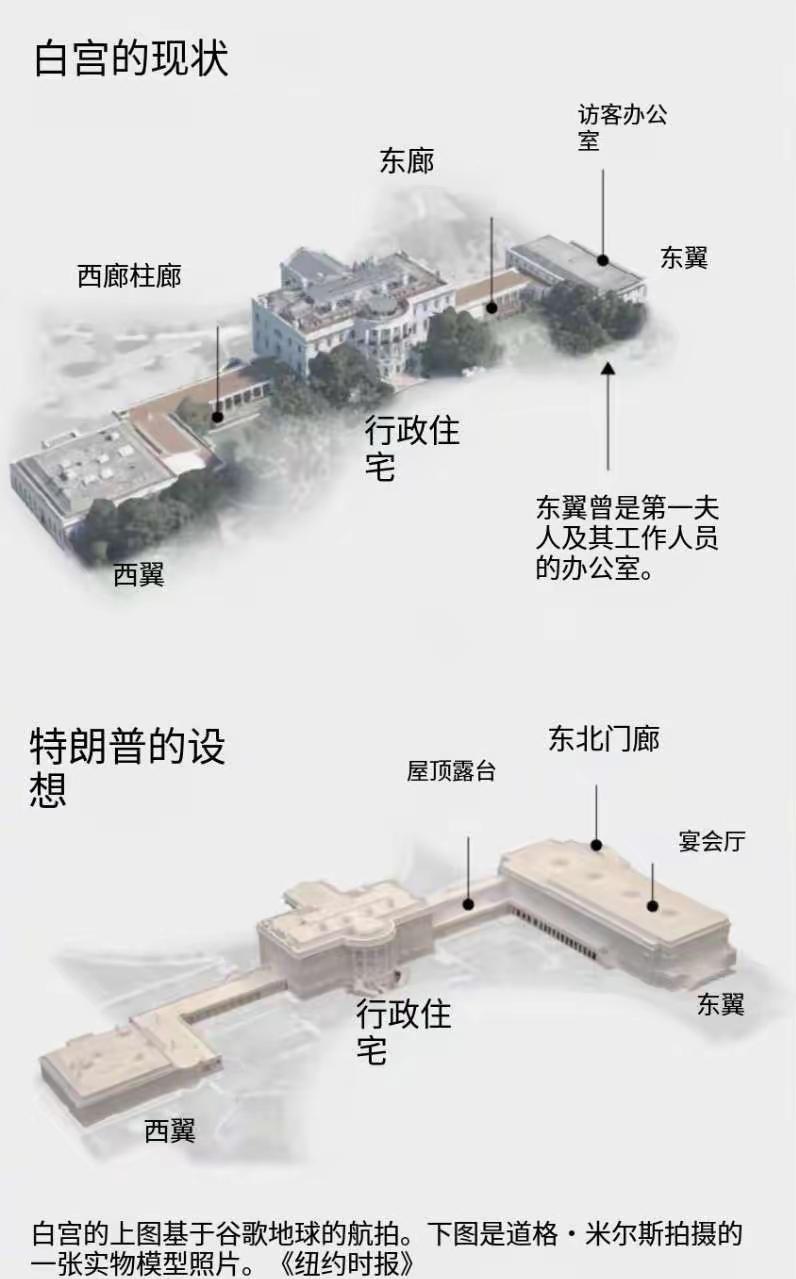

用户16xxx22
老一辈就说过“人离乡贱”,根系文化断层,新的圈子又天然隔离。
遛遛
80%不卷,那20%部分是真卷啊。
云横九派
“精英不过三代”这种现象在人类社会普遍存在
这个社会只认钱
回来的都是在美国混不下去的,稍微能混下去的都不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