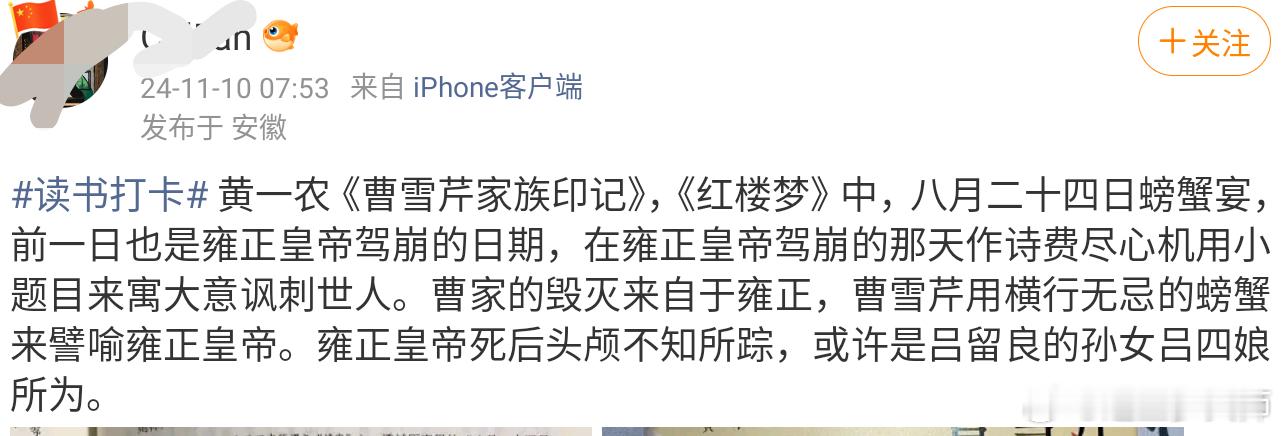"1942年,一名伪军师长派人送给粟裕一把伞,粟裕疑惑地打开伞一看,里面竟藏了一张纸,纸上的内容让粟裕吓出冷汗,他立即下令:“全军集合!” “报!那个大汉奸施亚夫派人送东西来了!”警卫员一声怒喝,将一把还在滴水的油纸伞“啪”地一声顿在桌角。伞面上的桐油在油灯下泛着冷光,水珠顺着伞骨滴在青砖地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的湿痕。 1942年深秋的苏中,日寇的“清乡”像篦子一样刮过田野,新四军一师的指挥部里,空气凝重得能拧出水。粟裕盯着地图上密密麻麻的日军据点,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就在半小时前,侦察兵刚报告南坎方向有日军异动,这个节骨眼上,“大汉奸”施亚夫送礼,是陷阱还是另有隐情? “晴天送伞,这戏码唱的哪一出?”粟裕走到桌边,伸手握住伞柄。 粗糙的竹节磨得掌心发疼,可重量却比寻常伞柄沉了几分。他拇指在伞柄根部摩挲,突然触到一处细微的接缝——多年带兵的直觉让他心头一紧。 “拿剪刀来!” “咔嚓”一声,中空的竹柄裂开,一个裹着蜡封的纸卷滚落在油灯下。参谋们瞬间围拢过来,连呼吸都放轻了。 纸条展开,字迹潦草却力透纸背:“小林信男四路合围,归途图已到手,电台有内鬼,速撤!” 粟裕的后背瞬间沁出冷汗。南坎会议的返程路线是绝密,连参会的团级干部都未必知情,日军怎么会这么快拿到?那个“内鬼”,竟藏在最核心的电台室? “传我命令!”他猛地一拍桌子,“所有电台即刻静默;返程路线全部作废,改走水网小道;保卫科立刻控制电台室,只进不出!” 骑兵通讯员策马冲出指挥部时,苏中行署主任管文蔚的船队离日军伏击圈只剩三里水路。当通讯员连人带马冲进芦苇荡,嘶吼着“停下!快靠岸!”时,管文蔚看见他胸前的伤口还在冒血——那是穿越封锁线时被子弹擦过的痕迹。 第二天,日军的重炮把原定路线炸成了焦土,却连新四军的影子都没看见。小林信男在电台里咆哮,骂着“废物”,而此时的施亚夫正坐在伪七师的师部,慢悠悠地用茶盖撇着浮沫。 这个被南通百姓戳脊梁骨骂“二狗子”的师长,谁也不知道他的党员证藏在床板夹层里,从1930年入党那天起,红色印章就没褪色过。 当年投诚汪伪时,他带着两三百号人,却敢吹“八千精兵”。为了圆谎,他让人对着《百家姓》编花名册,日军点验那天,故意安排手下在远处打冷枪,谎称“遭遇新四军偷袭”,吓得点验官连人数都没数清,直接给他封了中将师长,还拨了一整车武器。 “内鬼在电台”的线索,成了粟裕心里的刺。保卫科突击检查时,吴姓参谋的饭盒引起了注意——夹层里有张用米汤写的防区图,鞋底更藏着特高课的微型印章。铁证面前,这个每天给战友递烟的“老好人”,终于低下了头。 1944年冬夜,日军特高课的特务已经在师部周围布控,施亚夫知道,潜伏的日子到头了。他在伪军高层会议上突然拔枪,指着伪军长的脑袋:“想活命的,跟我打鬼子去!” 那夜的南通城枪声震天,2000多名伪军调转枪口,炸毁日军军火库,浩浩荡荡开进了新四军防区。当施亚夫撕下伪军制服,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粗布褂子时,迎接他的,是粟裕亲自递来的一碗热粥。 后来有人问施亚夫,忍四年骂名值不值。他指着墙上的地图:“你看这地图上的红圈,每个圈都是没被日军占去的村子——那就是值。” 2010年南京的病房里,96岁的施亚夫已经说不出话。护士整理遗物时,发现他枕头下压着一张泛黄的纸,上面是粟裕的笔迹:“你的伞,撑住了苏中半壁江山。” 如今那把油纸伞还在纪念馆里,伞骨上的裂痕像一道伤疤。参观者总会问:“这伞有什么特别?”讲解员会指着裂痕说:“当年就是从这里,撬出了一个民族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