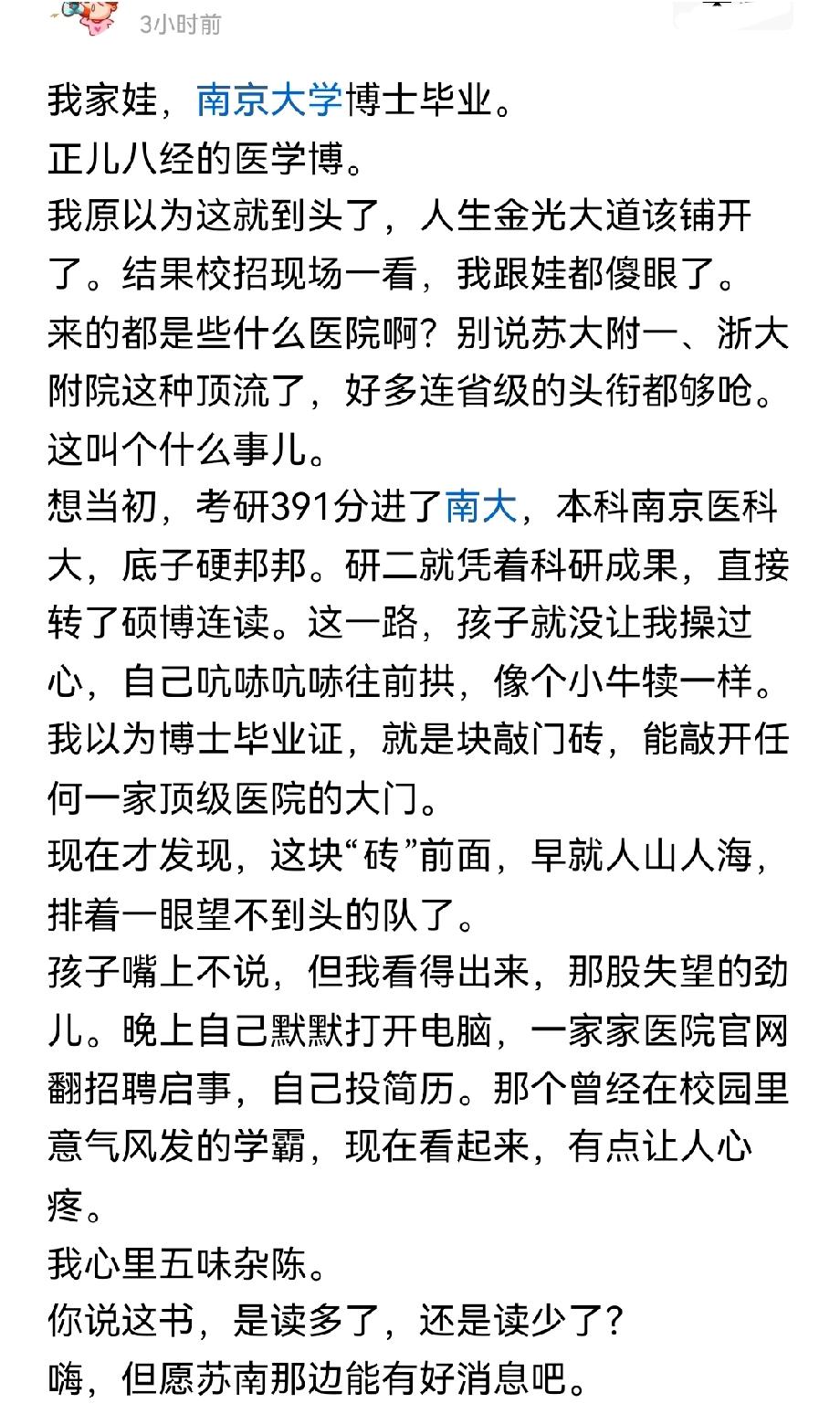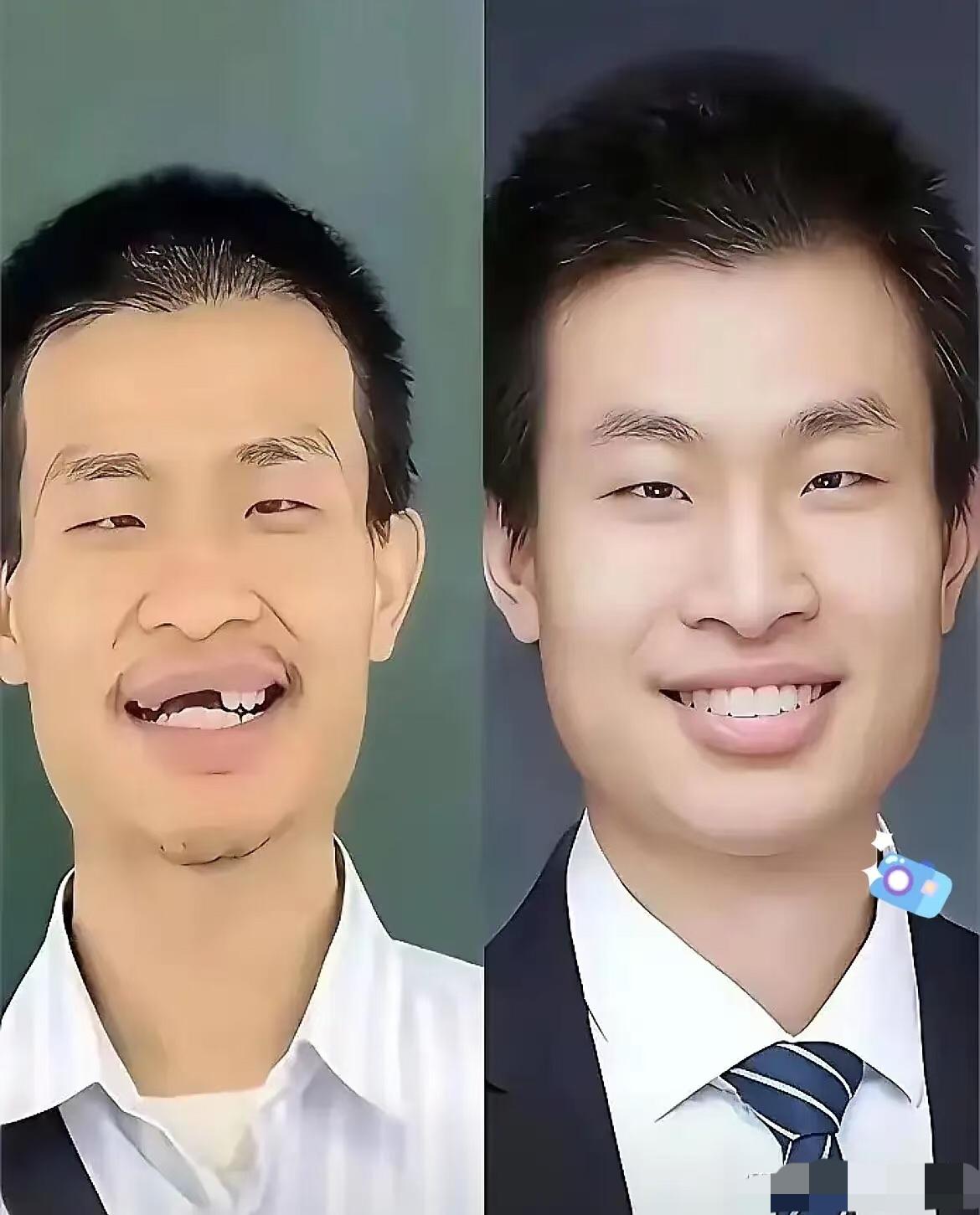看到一条消息:清华大学聘用了翁帆,我觉得这个安排是合适的。 她最早在汕头大学读英语系本科,那时候就没把自己局限在“会说英语”的层面,专业课成绩一直排在年级前几,还主动跟着老师做英语文学的课外阅读项目,比如整理过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翻译笔记。 上世纪末的高校校园里,外语专业学生多以“语言工具”为目标,翁帆却在笔记本上逐行标注雪莱诗歌里的隐喻——钢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混着图书馆旧木地板的吱呀响,成了她区别于同龄人的独特注脚。 她的学术路径始终带着一种“向下扎根”的执拗,从汕头大学的本科课堂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译校实践,再到清华大学的博士研究,每一步都踩在具体的文本与方法论上。 博士阶段选择托妮·莫里森的“身体叙事”作为研究切口,在当时的比较文学领域不算主流——多数研究者更关注主题思想或叙事结构,她却盯着小说里那些关于皮肤、伤痕、呼吸的描写,从身体符号里扒出文化权力的肌理。 那篇《论〈宠儿〉中身体符号的文化隐喻》后来被多位学者引用,不是因为选题讨巧,而是她在注释里列的23个原始文献版本对比,连莫里森手稿里的修改痕迹都做了梳理。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讲师招聘,从来不是“走个过场”。 学术委员会初筛时,教授们会把论文的引用文献挨个核查,连注释格式的规范性都算评分项;校外同行评议更像一场匿名答辩,有位参与评议的教授后来透露,“当时有篇论文被指出‘理论框架悬浮’,直接就淘汰了”。 翁帆能走到试讲环节,单是前期材料审核就已经过了五轮。 试讲那天她讲“翻译中的文化转码”,没用PPT,就带了本翻得卷边的《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那是她读研时参与译校的版本,里面夹着当年的工作笔记,泛黄的纸页上用不同颜色的笔标着词义辨析。 “‘龙’在中英文里的文化负载完全不同,直译会造成误解,意译又可能丢失意象,”她举的例子是自己译校时遇到的“东方龙”与“西方dragon”,连怎么和编辑争论三个回合才确定译法都讲了,台下有学生小声说:“比课本上的理论生动多了。” 有人说“她能留下肯定靠关系”,可清华大学的学术圈子最容不得这个。 人文学院有位退休教授在访谈里提过,“招聘投票时只要有一个人反对,就会启动二次核查”;翁帆的岗位所属的教学委员会,成员里有研究古典文学的、有搞现当代理论的,学科背景差异极大,能让所有人都点头,靠的绝不是“身份”。 杨振宁先生虽是清华大学荣誉教授,但他的研究领域在物理学,办公室在理科楼,和人文学院的招聘流程隔着好几个校区;翁帆入职那年,人文学院共招聘6名青年教师,另外5位分别毕业于北大、复旦、剑桥、伯克利,没人因为“家属身份”被额外关注——高校招聘的铁律是“专业对口、流程合规”,这在清华大学尤其严格。 她入职后带的第一届学生,毕业论文选题涉及从《红楼梦》英译本到奈保尔小说的跨文化解读,她逐篇批注的修改意见比论文本身还长。 有学生晒出她批改的作业,连“的、地、得”的用法错误都标了出来,旁边写着“此处用‘地’更能体现动作的状态——试着读三遍,感受语气差异”。 期末评教时,她的得分在全院青年教师里排第三,有学生留言:“上她的课,不敢糊弄,因为她比你还认真。” 总有人拿“家庭主妇”的标签质疑她,可学术界评价一个人的标准从来不是“身份”,而是“成果”。 她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翻译研究”,入选了年度优秀结项成果;合编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案例集》被多所高校用作教材,里面收录的27个案例,有19个来自她的课堂教学实践。 这些成果摆在那里,比任何“身份”都更有说服力。 或许我们该问:当一个人同时拥有多重身份时,我们究竟该用哪个标签定义她? 是“学者”,还是“某某的家属”? 清华大学的选择,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在学术的天平上,只有实力不会失重。 从汕头大学图书馆里整理诗歌翻译笔记的本科生,到清华大学讲台上带着学生啃词典的讲师,翁帆走的这条路,和所有靠学术立身的人一样,一步一个脚印。 那些质疑声或许还会有,但她的课堂、她的论文、她的学生,都在无声地证明:这个安排,确实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