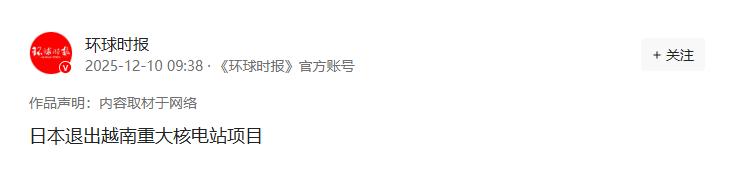日本退出越南重大核电站项目 2025年12月8日,日本驻越南大使伊藤直树的一句话,让持续十二年的越日核电合作戛然而止——日本正式退出越南宁顺2号核电站项目,理由是“工期过于紧凑”。 这个总装机容量达2至3.2吉瓦、原计划2035年投产的能源重器,曾被越南视为缓解电力短缺的“救命稻草”,如今却因日方一句“时间不够”陷入停滞。 消息传来,越南工贸部沉默不语,国家油气集团避而不谈,仿佛印证着这场合作从始至终的艰难。 故事要从越南的用电焦虑说起,作为三星、苹果等巨头的东南亚制造中心,越南过去十年GDP年均增长6.5%,工业用电需求激增3倍。 2023年夏季,胡志明市因电力短缺导致3000家工厂停工,河内居民经历每周三次限电。 更棘手的是,越南40%电力依赖水电,2024年湄公河干旱直接让发电量锐减25%。 这种背景下,核电被视为“稳定器”——宁顺1号、2号两座核电站若建成,将贡献全国15%的基荷电力,相当于每年减少1200万吨煤炭消耗。 但越南的核电梦从一开始就充满波折,2010年代初,越南分别与俄日签约建设宁顺1号(俄制VVER堆型)和宁顺2号(日制ABWR堆型),熟料2011年福岛核事故引发全球核电恐慌,越南民众上街抗议,政府于2016年紧急叫停项目。 这一停就是六年,直到2023年电力缺口突破10%,河内才重启核电计划,恳请俄日回归。 然而时过境迁,日本东芝、日立等企业因福岛事故元气大伤,国内核电人才流失近40%,连成熟的反应堆型号都拿不出手。 今年2月,一名日本官员私下交底:“宁顺2号最快2036年运营,实际可能拖到2040年。” 工期矛盾的背后,是日越对“时间”的不同认知,越南的电力规划像在和时间赛跑:2030年工业产值要翻番,2035年碳中和目标需要清洁能源支撑。 河内要求2026年前完成项目审批、2030年动工,留给日本的准备时间只有四年。 但日本企业测算,从厂址复核、设备定制到人员培训,至少需要八年——福岛事故后,日本核监管标准提升30%,海外项目需额外满足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三重审查。 一名参与前期评估的工程师透露:“宁顺厂址曾是火山活动带,地质勘查数据缺失,重新勘探就要两年。” 更深层的矛盾藏在日本的战略收缩里,尽管岸田政府喊出“核电出口大国”口号,但福岛的阴影从未消散。 2022年,日本国内核电占比从事故前的30%降至6%,重建本土反应堆消耗了90%的核电工程师。 东芝能源部门负责人曾坦言:“我们连国内的滨冈核电站重启都顾不过来,哪有精力管海外项目?” 这种困境在宁顺2号上尤为明显:日本承诺的ABWR堆型,自2016年后再未在海外落地,核心部件供应商半数已转产可再生能源设备。 微妙的是,日越关系近期的摩擦让合作雪上加霜,2025年河内禁售燃油摩托政策,直接冲击占据越南80%市场的本田公司。 日本使馆9月发函抗议,至今未获正式回复,尽管伊藤直树强调“核电退出与摩托政策无关”,但河内街头本田经销商的抗议横幅,与日本使馆的沉默形成刺眼对比。 这种“经济合作遇冷”的氛围,让本就脆弱的核电谈判失去了缓冲空间。 越南现在面临的,是能源规划的“多米诺骨牌”。宁顺2号退出后,2035年电力缺口将扩大至22%,相当于每年多烧1800万吨煤。 更麻烦的是,宁顺1号的俄方合作伙伴至今未表态——俄罗斯原子能集团正忙于土耳其核电站项目,对越南的“二次邀约”态度暧昧。河内曾指望“双保险”,如今变成“零保险”。 不过,市场空白很快被盯上,法国EDF带着小型堆SMR-160、韩国KHNP拿着APR-1400、美国NuScale推销模块化反应堆,均承诺“2035年前投产”。 但越南的顾虑同样现实:法国堆型需要新建海水淡化厂,韩国设备成本比日本高35%,美国技术尚未在东南亚验证过。 更关键的是,越南核电法规定“外资持股不得超过51%”,这让习惯控股的美法企业犹豫不决。 日本并非完全离场,伊藤直树透露,日方正考虑以“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卷土重来——这类300兆瓦级的“核电积木”,建设周期仅需四年,且对地质要求更低。 越南中部沿海有17个SMR潜在厂址,其中3个已完成初勘。 但SMR的问题在于“不够解渴”:宁顺2号单座可满足300万户家庭用电,而SMR需要建10座才能达到同等规模,土地、审批成本成倍增加。 这场十二年的合作拉锯,最终暴露的是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的残酷现实,越南需要的不仅是技术,更是能与时间赛跑的“战略耐心”——当日本因福岛后遗症步履蹒跚,当欧美资本带着附加条件蜂拥而至,河内或许不得不重新审视:在工业化与碳中和的夹缝中,是否真的存在“完美的能源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