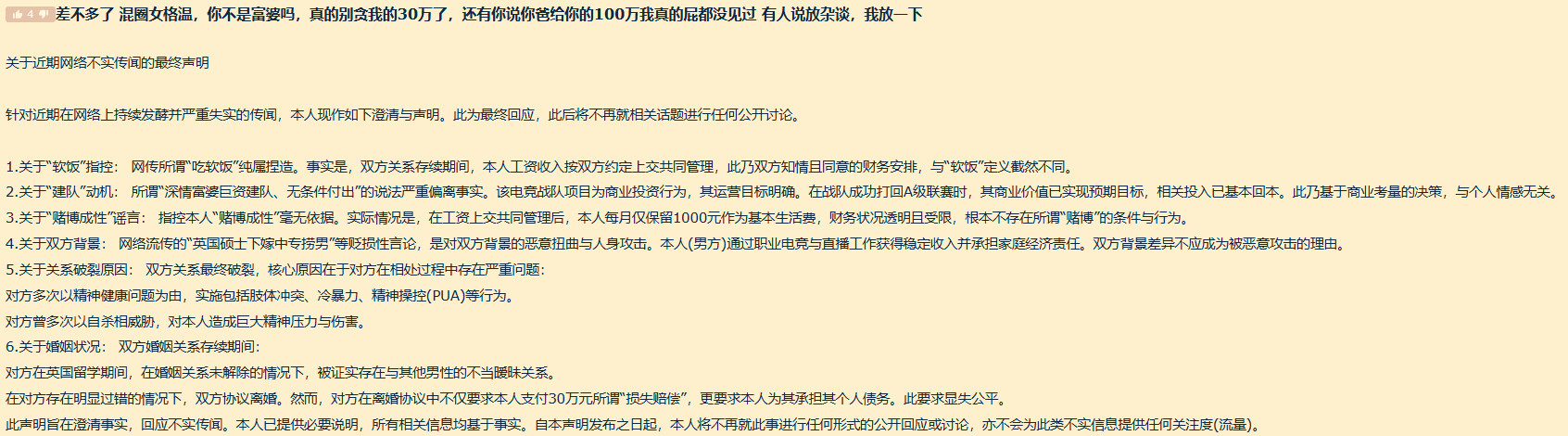1938年,一名外国婴儿在天津的一家医院出生。可他的父母因为着急要回国,直接把他丢在了医院。 1938年的天津,兵荒马乱。一家教会医院里,一对外国夫妇生下了一个男婴。没人知道他们当时是怎么想的,或许是急着逃离战火,或许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反正这俩人扭头回国了,把这刚出生的肉团子扔在了医院里。 这孩子命不该绝。一对善良的中国夫妇——李毅之和赵秀珍,把他抱回了家。 他的养母赵秀珍,大字不识几个,就是个普通的中国妇女。小时候李忆祖头发黄、鼻子高,出门总被胡同里的孩子起哄叫“小洋鬼子”。他哭着回家找娘,赵秀珍也不讲什么大道理,就告诉他一句话:“人得有骨气,不管长啥样,心正了,腰杆子就硬。” 养父母给他起名“忆祖”,这名字有讲究。不是让他回忆那个抛弃他的外国祖宗,而是让他记住,这片养育他的土地,才是他的根。 李忆祖这书读得顺风顺水,一路念到了北京地质学院。按理说,这是个在那会儿金贵得不行的大学生,又是北京户口,毕业了留在皇城根下,进个部委或者研究所,那日子得多舒坦? 可这老爷子年轻时候,那叫一个“狂”。 那是1961年,他快毕业了。学校请了两个刚毕业的师兄回来作报告。这俩师兄也是实在人,在台上那是唾沫横飞,吹牛说青海风景美得像画一样,又说晚上睡帐篷多刺激,连大狗熊都能摸进门来。 台底下的同学听得一愣一愣的,大伙儿心里可能都在犯嘀咕:这哪是工作啊,这是玩命啊。 可坐在台下的李忆祖,眼睛亮了。他心里琢磨:哎呦,这生活带劲,适合我这性格! 就这么着,毕业分配志愿表发下来,他大笔一挥,第一志愿填得死死的:去新疆,去最艰苦的地方。 那是1962年,24岁的李忆祖背着行囊,告别了养育他的北京城,一头扎进了新疆的茫茫戈壁。这一扎,就是将近60年。 咱们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想象当年的地质勘探是个什么苦差事。现在的户外探险那叫“驴友”,那是花钱找乐子。当年的地质队,那是在玩命。 李忆祖分到了新疆煤田地质局156队。这工作就是在大山里转悠,找矿。 这一进山,就是半年。从4月积雪刚化,一直干到9月大雪封山。饿了,就啃两口干得像石头一样的馕,抓把雪塞嘴里顺下去;困了,找个背风的石头窝子,铺上羊皮袄就睡。 李忆祖后来回忆起那段日子,说得那叫一个轻描淡写。他说有一次在阿尔金山无人区,他骑着毛驴去考察。那毛驴也是个倔脾气,半道上把他掀翻在地,摔得七荤八素。结果屋漏偏逢连夜雨,他又发起了高烧。 在海拔4000米的高山上发烧,那是要命的事儿。可为了不耽误进度,他硬是让同事搀着,一步一步挪到了监测点,把数据记录完了才肯下山。 这是什么精神?那时候的人,你说他傻也好,轴也罢,他们心里真就装着“祖国”这两个字。 他在野外跑了22年。这22年里,他那是“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他学会了骑马、骑骆驼,学会了怎么在荒野里辨别方向,甚至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新疆土话。 这么苦,他就没想过回北京? 其实机会多得是。按政策,他这种家庭情况,要把户口调回北京也不是办不到。但他一次次都拒绝了。 他说:“北京是我的故乡,但新疆是我的家。这里的山山水水我都跑遍了,舍不得。” 等到上世纪80年代,李忆祖跑不动野外了,组织上让他去子弟学校当校长。 你以为这老爷子要开始养老了?那你就错了。他这辈子就不知道“闲”字怎么写。 退休后,他干了一件特“潮”的事儿——搞科普。 他觉得现在的孩子,离大自然太远了,离科学太远了。他就自己动手做教具。讲磁悬浮,他就找俩磁铁、一个发电机,叮铃咣啷一阵捣鼓,一通电,转起来了!孩子们看得眼珠子都直了,比打游戏机还过瘾。 为了讲课,这老头愣是学会了用电脑,做了几百个PPT,写了80万字的讲稿。80万字啊,朋友们,这相当于写了两三部长篇小说! 更绝的是,2011年,他都73岁了,还被央视《地理中国》栏目请去当顾问。 这一去又是8年。 他又一次踏上了那片他年轻时用脚丈量过的土地。这时候的他,腿脚早就不利索了,膝盖磨损严重,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但只要镜头一开,只要看见那些奇特的地质地貌,这老爷子眼里的光,比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还亮。 他指着那些山川河流,如数家珍:“这块石头是啥时候形成的,那条河道是怎么变迁的……”那神情,就像是在介绍自家的后花园。 前两年,有记者去采访他。看见83岁的他住在一个只有60平方米的老房子里。屋里没什么像样的家具,全是书,还有一堆堆的光盘和录像带。 那是他一辈子的心血。 有人问他:“李老,您这一辈子,后悔过吗?要是当年留在北京,现在怎么着也是个享清福的高干了吧?” 李忆祖笑了,那满头的卷发跟着颤悠。他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是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我就是个普通的地质队员,做了我该做的事。回头看看这辈子,我觉得我没白活,无愧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