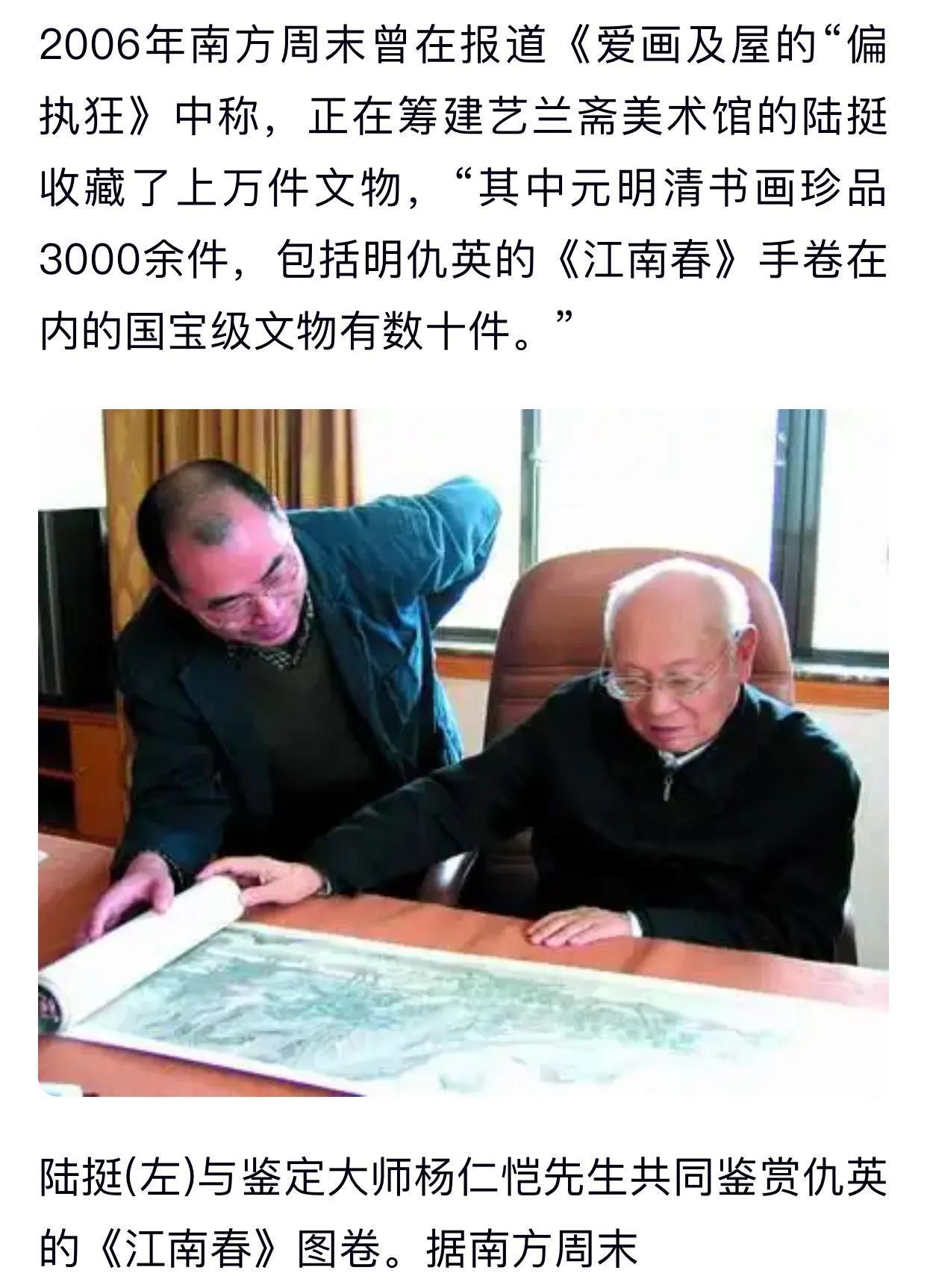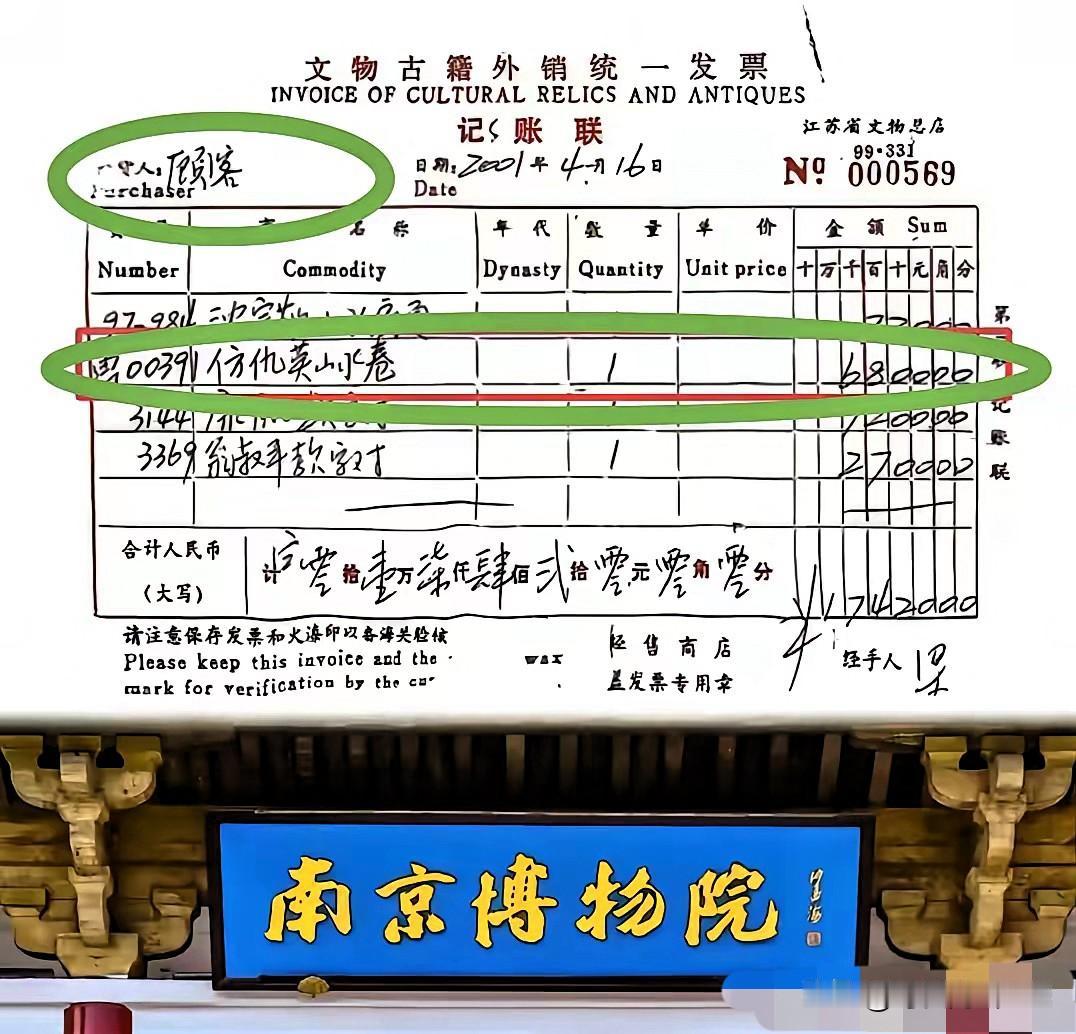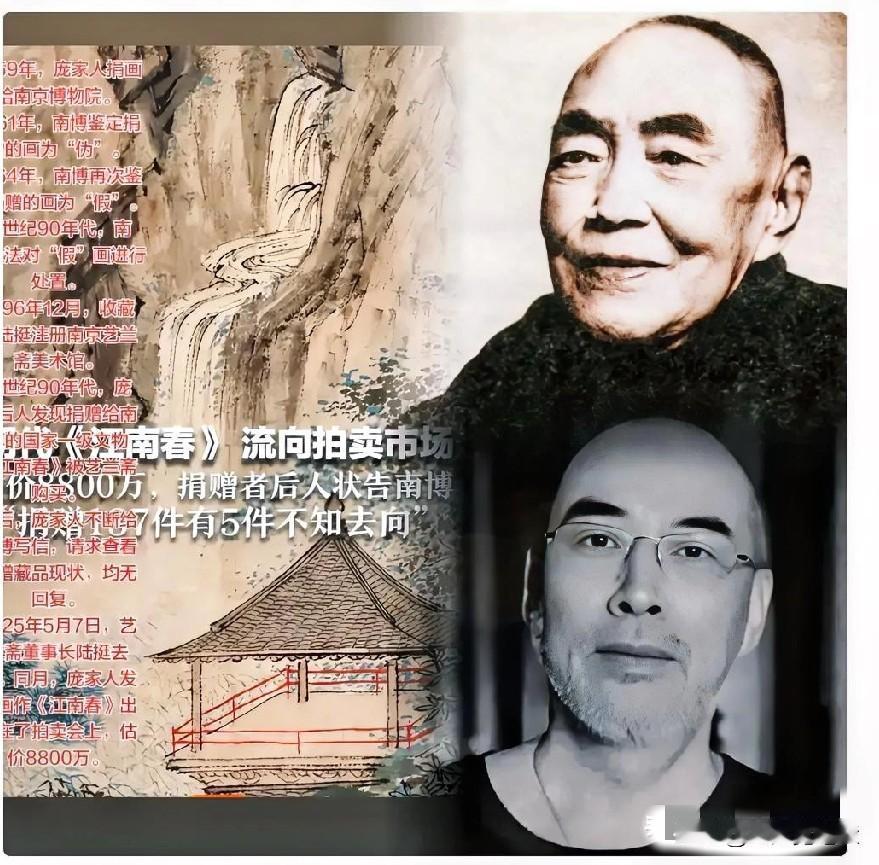一次,富豪买了张大千一幅画,回家却发现是赝品。 换作旁人,多半要揪着卖画的人讨说法,可这位富豪盯着画看了半晌,突然拍了桌子,“这造假的小子,笔力竟比真迹还野!” 那时张大千刚到上海混饭吃,二十出头的年纪,连画案都凑不齐整。 石涛的画在市面上炒得火,一张真迹能换半条街的铺面,他只能对着画册死磕。 矿物颜料买不起,就用胭脂调朱砂;清代宣纸弄不到,拿陈年毛边纸用茶水渍黄了充古纸。 原以为能蒙混过关,没想到栽在了买家女儿手里。 打破这场骗局的是富豪女儿张婉君。 小姑娘刚从美术专科学校回来,接过画轴只扫了一眼,就指着提款处说:“石涛的竹子是含着气的,这画里的竹叶,像被风吹僵了的鸡毛。” 她爹起初不信,翻出家里藏的《搜尽奇峰图》比对,果然,真迹里山石的皴法像老树皮裂着缝,仿作却光溜溜的,少了那股子孤倔劲儿。 谁都以为富豪要动怒,他却让人把张大千请来。 一见面,没提退钱的事,反倒推过去一叠银票:“你仿石涛,形似差口气,可这腕力藏不住。 敢不敢跟我女儿学三个月?”我觉得这种胸襟,在那个版权意识模糊的年代,更像一场豪赌,赌一个年轻人的未来。 张大千后来常说,那天他站在张家客厅,看着满墙的真迹,突然明白自己以前只学了皮毛。 张婉君教他辨画,不看笔法看“气”。 她把石涛的《竹石图》挂在窗边,让晨光斜照在宣纸上:“你看这墨色,浓的地方像乌云压顶,淡的地方能透进光来,这才是‘干裂秋风,润含春雨’。” 张大千跟着她临摹真迹,渐渐懂了石涛画里的郁勃,不再执着于形似。 半年后,他画出的第一幅原创山水,被富豪收进了藏画楼。 旁人都以为这对年轻人会走到一起,可张大千那时已有家室。 有次张婉君拿着他新画的荷花说:“这花瓣尖上的红,像哭过的眼睛。” 他没接话,只把画收进了匣子里。 后来他去北平发展,临走前想把那幅荷花送给她,却听说她已经闭门谢客。 晚年张大千在巴西画《爱痕湖》,泼彩里总藏着几支荷花。 有访客问起,他指着画中孤舟:“当年有人教我,画里的留白不是空的,是没说出口的话。” 那幅画后来拍了上亿,可懂行的人说,最值钱的是船边那片淡墨,像极了当年张婉君书房窗外的月色。 晚年张大千再画荷花,总在花瓣尖点一笔胭脂红。 他说那是跟人学的“藏情”,就像当年张婉君指出的“僵竹叶”,真正的好画,都带着画者的心跳。 那笔胭脂,是他欠知己的一声谢谢,也是艺术里最珍贵的“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