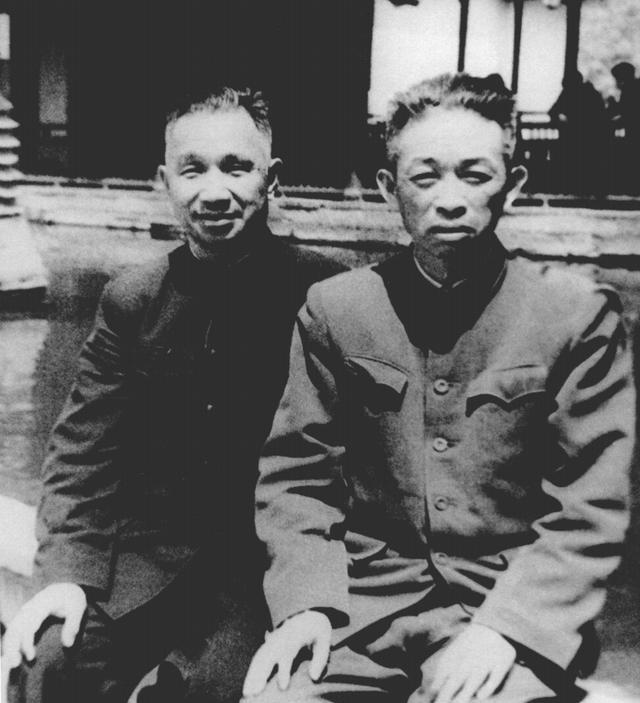1952年,郑洞国调去北京任职,妻子却嫌弃离家远,工资低,不肯跟去,一年后,还提出离婚,改嫁富商,谁知,20年后,又哭求复婚。 1973年的北京胡同,槐树叶子落了一地碎金。陈碧莲裹着洗得发白的旧棉袄,在四合院门外转了第八圈。她怀里揣着张泛黄的老照片,是1943年在滇缅战场拍的——那时她穿着蓝布旗袍,站在郑洞国身边,军靴上还沾着怒江的泥点子。 院门“吱呀”开了。郑洞国拄着拐杖走出来,灰中山装的领口别着枚政协委员的徽章。陈碧莲突然冲上去,“噗通”跪在青石板上,照片从怀里滑出来,飘到郑洞国脚边。 “桂庭……我错了……”她的哭声像被风吹散的棉絮,“让我回来吧,哪怕给你端茶倒水……” 郑洞国弯腰捡起照片。照片上的姑娘正仰头对他笑,眼里的光比战场上的信号弹还亮。那是她瞒着家人,坐运输机飞越驼峰航线来看他的样子——机仓缺氧让她晕得天旋地转,却死死抱着给他带的上海肉松。 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郑洞国的指腹擦过照片上姑娘的脸,想起1952年那个上海的清晨。 那天他刚接到水利部调令,兴奋地在屋里转圈:“碧莲你看,北京的房子带院子,能种你喜欢的栀子花!” 陈碧莲却坐在梳妆台前涂口红,镜子里映出她新烫的波浪卷发:“要去你自己去,”进口香水的味道飘过来,“北京风沙大,我这皮肤可受不住;再说,厅级参事的工资,够买几瓶巴黎香水?” 郑洞国愣住了。他记得她曾把最后一块干粮塞给他,说“你打仗要有力气”;记得她在防空洞里抱着他的胳膊发抖,却说“只要跟你在一起就不怕”。现在,她连搬家都嫌麻烦。 他独自北上的火车上,行李箱里躺着半件她织了一半的毛衣,针脚停在第三十二行。郑洞国摩挲着毛衣针,心里存着念想:等她气消了,总会来的。 一年后的离婚协议书,像把钝刀子割开了他的念想。陈碧莲的字迹娟秀依旧,却写着“沪上生活奢靡,难改;君之薪资,不足养家”。郑洞国在“同意”栏签字时,钢笔尖把纸戳出个小洞——那天北京下了雪,他把半件毛衣锁进樟木箱,压在黄埔军校的毕业证书下面。 后来听说,她嫁给了上海做进出口生意的王老板。报纸上登过照片,她穿着貂皮大衣,挽着王老板的胳膊走进和平饭店,手腕上的金镯子晃得人眼晕。郑洞国只是把报纸叠起来,塞进炉子里——那年他刚被毛泽东主席邀请参加中南海家宴,主席给他夹红烧肉时说:“洞国啊,你是识大体的人。” 陈碧莲的好日子,在1966年断了线。王老板偷税漏税的账本被翻出来,洋房汽车全充了公,连她压箱底的翡翠镯子都被抄走了。她搬进弄堂亭子间,靠给人缝补衣服过活,手指被针扎得全是小孔。 20年光阴,把她从“怒江之花”磨成了胡同里的老妇人。当她打听到郑洞国的住址,揣着那张老照片找上门时,看见的是他身边站着的顾贤娟——那个给他补毛衣、陪他逛颐和园的女人,手里牵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甜甜地喊“爸爸”。 郑洞国沉默了很久,最后轻轻扶起她:“起来吧,地上凉。” 他从口袋里摸出个信封,塞进她手里,“这是些钱,你先安顿下来。” 信封上印着“全国政协”的抬头,边角有些磨损。 陈碧莲后来在街道工厂缝手套,缝纫机是郑洞国托人送来的“蝴蝶牌”。每个月领工资时,她都会想起那天郑洞国说的话:“日子要往前过,回不去了。” 只是偶尔,她会对着老照片发呆——照片上的姑娘怎么也想不到,当年用命守护的爱情,最后竟败给了梳妆台上的那瓶进口香水。 郑洞国去世后,女儿在樟木箱底发现了那半件毛衣。针脚歪歪扭扭的第三十二行,还别着枚生锈的毛衣针。旁边压着张字条,是郑洞国的笔迹:“有些线头断了,就接不回去了。” 字条下面,是陈碧莲后来托人送来的栀子花干,花瓣早已褪色,却还留着点淡淡的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