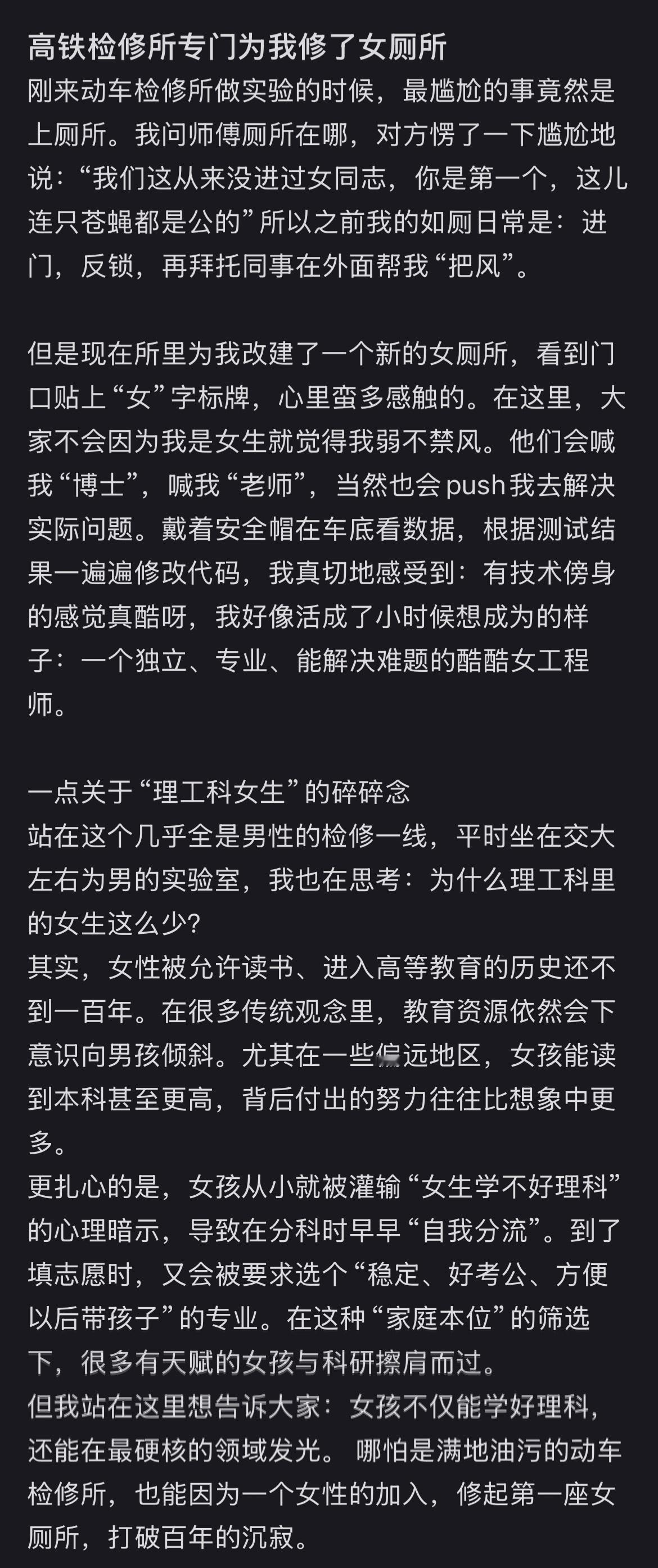公园长椅上,那个大爷纹丝不动。 他不是来晒太阳的,也不是来等人的。他手拄着拐杖,背微微弓着,像一尊雕塑。只有那双浑浊的眼睛,在老花镜后面,像雷达一样扫过每一个从他面前走过的年轻身影。 一个穿着碎花裙子的姑娘,耳机里放着歌,轻快地从路口拐过来。 几乎是瞬间,那双眼睛就锁定了她。 大爷的头没动,脖子也没转,但那道目光像一根无形的线,从镜片后射出,牢牢地粘在姑娘的裙摆上,跟着她移动,一寸,又一寸。他旁边的另一个大爷用胳膊肘碰了碰他,他像是没感觉到,整个身体微微前倾,攥着拐杖头的手,指节都绷紧了。 直到那个身影彻底消失在街角,他才长长地、几乎听不见地呼出一口气,身体重新陷进椅子里。 他转过头,对老伙计含糊地嘟囔了一句:“你看,年轻就是不一样,走路都带风。” 所以,这道追随了一整条街的目光,到底是在欣赏一幅画,还是在追忆一场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