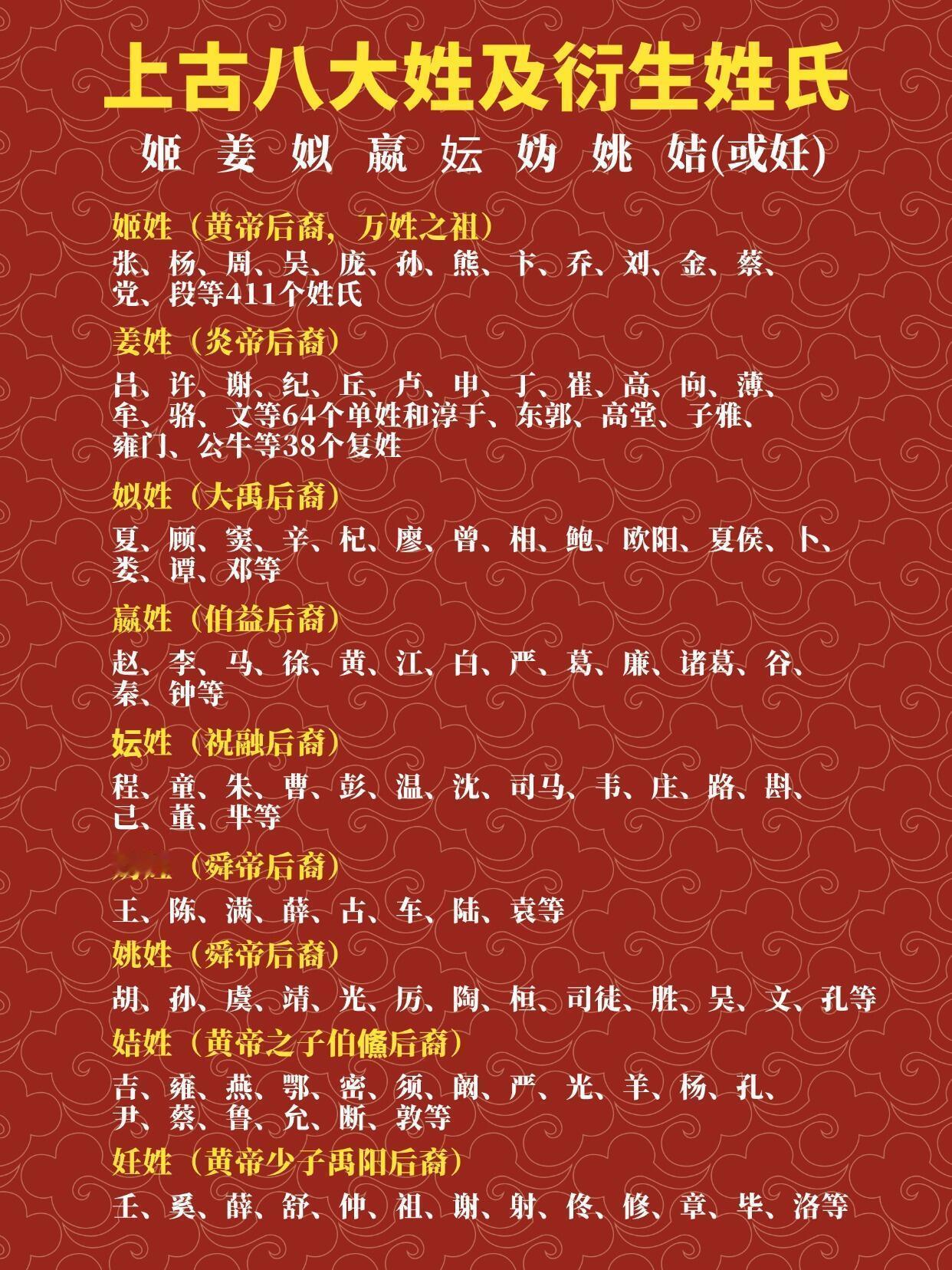古代把戏子划为下九流,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戏子本就是不务正业之人,他们不从事生产经营之道,而是专门迎合达官贵人,以此来获取衣食。 这话放在古代的社会语境里,能找到现实依据,却绝不是绝对的真理。要搞懂“下九流”的分类,得先看清古代的社会底色——农耕文明里,“男耕女织”才是主流,能种出粮食、织出布匹、造出器物的职业,才被视作“正业”,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农、工、商,尚且排在“士”之后,更别说靠“卖艺”为生的戏子。 古代的戏班,大多是流动的。戏子们背着行囊、扛着行头,走村串户,哪里有庙会、哪里有达官贵人的寿宴,就往哪里去。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没有稳定的收入,全靠台下看客的赏钱过活。达官贵人点一出戏,赏银能让戏班活上半个月;若是遇上灾年,百姓连饭都吃不上,谁还有闲钱看戏,戏子们就只能饿着肚子赶路,甚至冻饿而死。 有人说他们“迎合达官贵人”,这话没说错,却忽略了背后的无奈。晚清时,北京城里有个叫“玉春班”的戏班,班主李老根带着二十多个徒弟,最小的才八岁。为了能在王府的寿宴上唱一出,李老根提前半个月就带着徒弟们排练,最受欢迎的武生小三子,为了练一个空翻动作,摔断了腿,还强撑着上台。 寿宴上,王爷看得高兴,赏了十两银子,李老根捧着银子,当场给王爷磕了三个头——那十两银子,能给受伤的小三子治腿,能让整个戏班熬过寒冬。 可要说戏子“不务正业”,就太片面了。古代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戏曲是老百姓唯一的娱乐,也是他们了解历史、明辨是非的窗口。戏班里唱的《霸王别姬》,让百姓知道了忠义;唱的《窦娥冤》,让百姓看清了官场黑暗;唱的《花木兰》,让百姓懂得了家国情怀。这些戏文,不是简单的“迎合”,而是戏子们用唱念做打,把历史故事、民间疾苦搬上舞台,藏着对世道人心的观察。 清代有个叫程长庚的戏子,被称作“京剧鼻祖”。他出身戏班,自幼学戏,练就了一副“脑后音”,唱出来的老生唱腔,浑厚有力,传遍京城。可他从不是只会迎合达官贵人的角色。 有一次,一位权贵点戏,非要让他把《四郎探母》里的“杨四郎”改成投降的反派,还许诺给重金。程长庚当场拒绝:“戏文里的忠义不能改,改了就不是戏,是误人子弟!”权贵恼羞成怒,下令封杀他的戏班。程长庚宁愿带着徒弟们去乡下唱戏,也不愿妥协,他常对徒弟说:“我们唱的不是戏,是良心,不能为了钱丢了根本。” 戏子的苦,外人很难体会。学戏的孩子,大多是穷苦人家的孩子,被父母送进戏班,从小就过着“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日子。天不亮就起来吊嗓子,压腿、下腰、翻跟头,稍有不慎就会被师傅打骂。很多戏子练坏了身体,到老了唱不动了,就被戏班抛弃,只能靠乞讨度日。他们“迎合”达官贵人,不过是为了活下去,可在活下去的同时,不少人还守着心里的底线,守着戏曲的尊严。 古代把戏子划入“下九流”,本质上是等级社会的偏见。士大夫们坐在台下看戏,享受着戏子带来的娱乐,却又鄙视他们的职业,觉得自己“劳心者治人”,戏子“劳力者治于人”,甚至不准戏子和良家女子通婚,不准戏子参加科举。这种偏见,忽略了戏子们的付出,也否定了戏曲的文化价值。 就像明末清初的柳敬亭,本是说书人,也算“戏子”的一种。他说书时,能把历史人物讲得活灵活现,连东林党人、抗清志士都爱听他说书。他借着说书,痛斥奸臣当道,歌颂民族英雄,鼓舞了不少百姓的抗清斗志。后来清军入关,柳敬亭宁愿归隐山林,也不愿给清军说书,宁愿饿死,也不做亡国奴的戏子。这样的人,难道能算“不务正业”? 时代变了,“下九流”的说法早就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现在的戏曲演员,是国家一级演员,是非遗传承人,他们坚守着传统文化,把戏曲艺术发扬光大。可回头看古代的戏子,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不务正业”来评判他们。他们在艰难的处境里,用艺术慰藉了百姓的心灵,传承了文化的火种,甚至在关键时刻,守住了民族的气节。 职业从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谓的“正业”,也从来不是靠是否创造物质财富来定义。古代的戏子,用一生证明了:靠手艺吃饭、靠良心做事,就不是“不务正业”;能给他人带来快乐、给社会带来价值,就值得被尊重。那些嘲笑戏子“下九流”的人,恰恰忘了,真正的高贵,从来不是职业带来的,而是人格和操守带来的。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