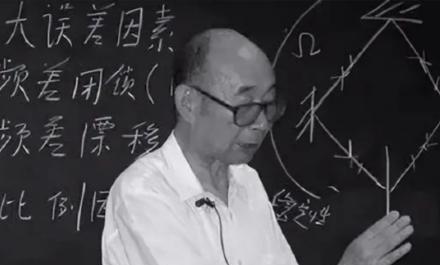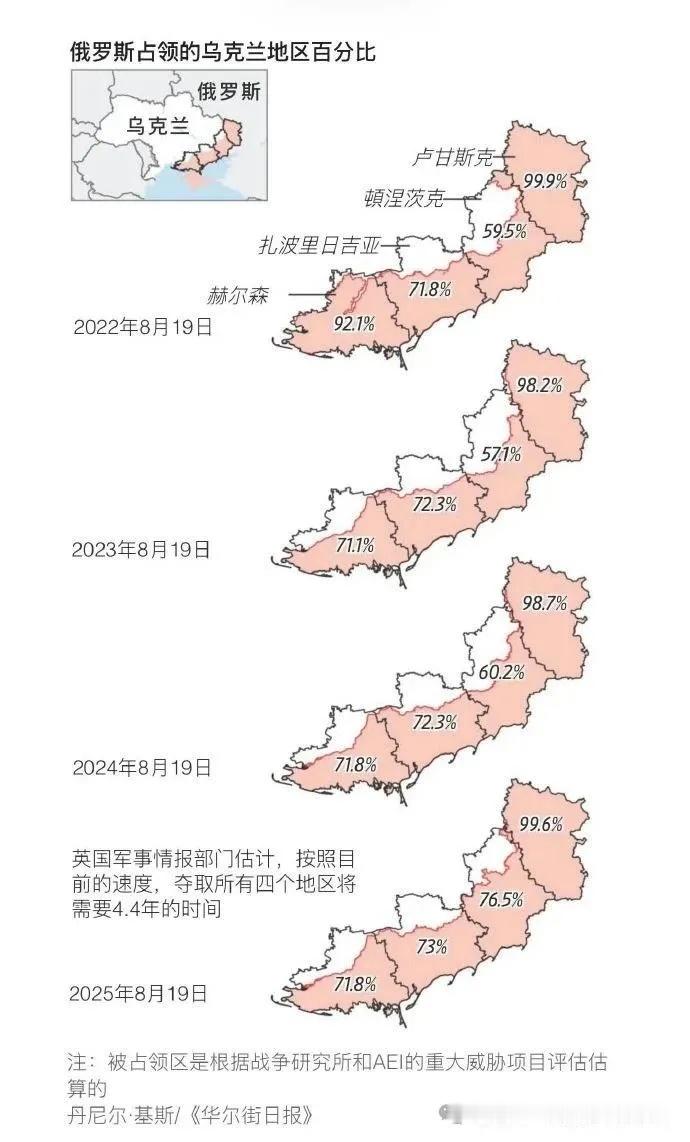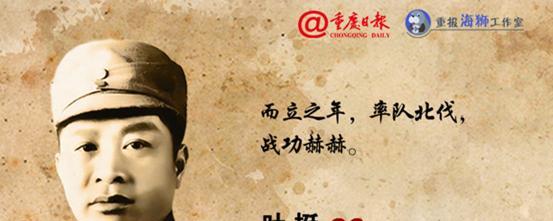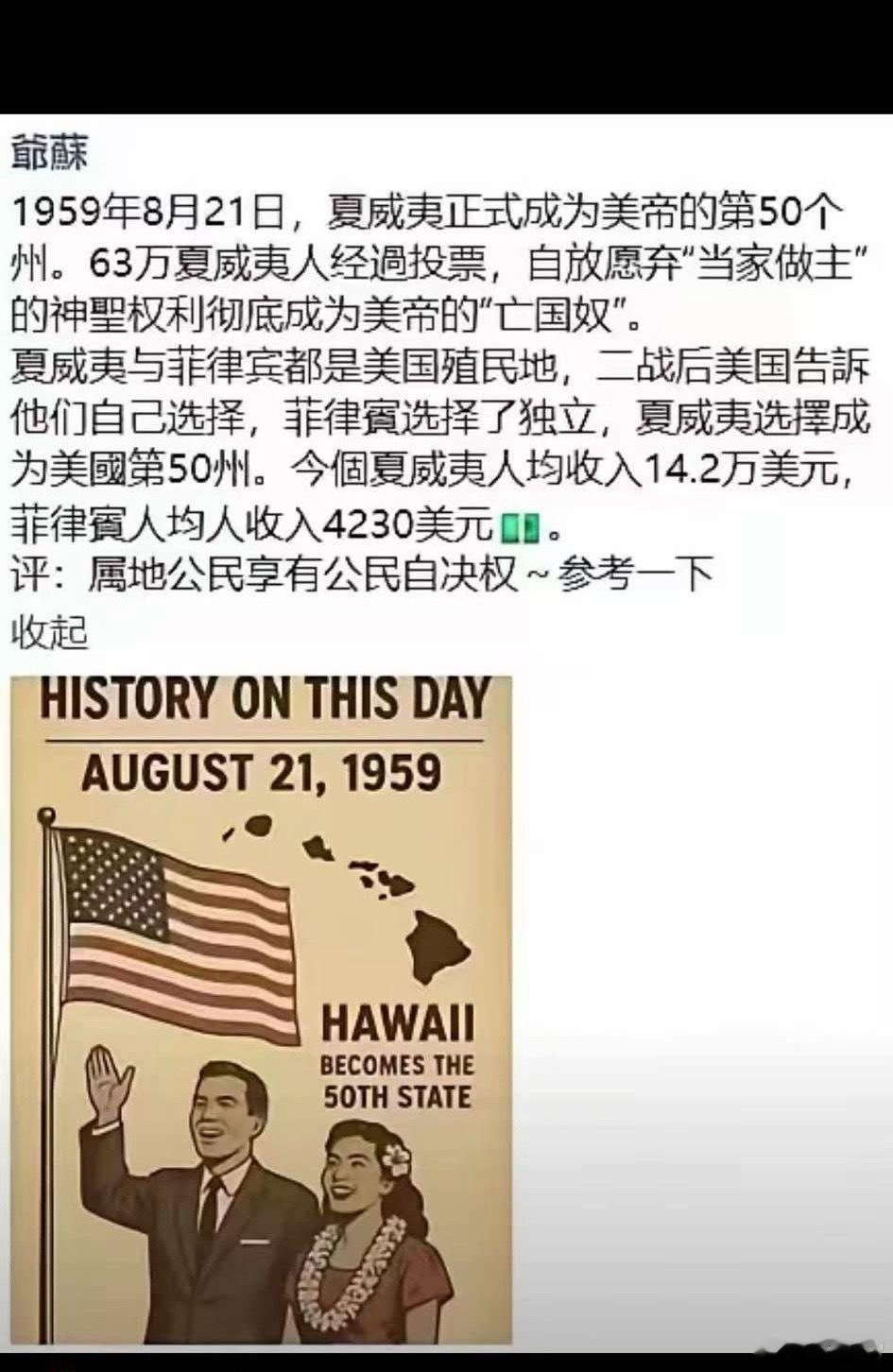“我花了20年时间,花了国家那么多钱,搞成这样,我是有罪的,”1993年冬天,高伯龙在实验室里盯着那台“罢工”的激光陀螺工程样机,声音沙哑地对团队成员说出这句话。 高伯龙,这名字如今被尊为中国激光陀螺的奠基人,他的一生,基本跟激光陀螺画上了等号,这玩意儿是高精度武器的“火眼金睛”,能让导弹精准命中,让潜艇在深海找准方向,让卫星在太空稳稳当当。 它的原理是用光束在转动中产生的频率差,感知物体在空间的位置,堪称导航技术的顶峰,可在上世纪70年代,这对中国的科研团队来说,就是一片没人走过的荒地。 1971年,钱学森递给国防科技大学两页纸,上面写着激光陀螺的原理,任务就这么开始了,那时候,中国工业底子薄,实验设备简陋,连像样的实验室都没有。 高伯龙接下这烫手山芋,带着团队从零开始,甚至是从负数起步,没有地方做实验,他们就把废弃食堂改成实验室,没有精密设备,就用建筑工地的废料搭实验平台。 他常在雨中摔倒,爬起来,捡大理石废料,只为撑起光路系统,工人们看他辛苦,冒雨帮他装车,可谁能想到,这些不起眼的废料,托起了中国军事科技的眼睛。 高伯龙的路不好走,1928年,他生在广西岑溪,1947年考进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时是全系仅有的两个优等生之一,本想搞理论物理,却被分配到应用物理,后来又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量子力学、统计力学。 直到1971年,43岁的他调到国防科技大学,接手激光陀螺项目,才算找到人生使命,那一刻,他不再是讲台上的老师,而是战场上的斗士,肩上扛着为国铸造“至强之光”的重担。 激光陀螺的研制,难如登天,光、机、电三领域技术要融为一体,每步都像在刀尖上跳舞,手工打磨一个激光环形器的小孔,得花半个月。 一个关键技术,可能耗一年多才找到突破口,高伯龙搞的四频差动激光陀螺,是中国独创的路子,避开了美国的套路,降低了工艺难度,但也意味着没任何经验可抄。 1972年,他写出《环形激光讲义》,成了这领域的理论基石,可理论只是开始,工艺才是硬仗,超抛加工、超抛检测、高精度反射率测量,每关都像座大山,高伯龙和团队一次次失败,一次次重来,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 1984年,实验室样机通过鉴定,算是个大突破,可质疑声马上来了,美国放弃了同类型激光陀螺,有人冷笑:“国外有的你们不干,国外干不成的你们倒去干?”高伯龙回得简单:“外国有的,我们得跟上,外国没有的,我们也得有,” 1994年,全内腔四频差动激光陀螺工程样机通过鉴定,中国成了第四个独立掌握这技术的国家,耗时23年。 高伯龙没停下,1994年后他又盯上了新型激光陀螺,想解决损耗和温度敏感性问题,适应战场的复杂环境,国外技术封锁得死死的,他只能看一张模糊的图片,可他还是带着团队没日没夜地干。 2010年,他指导的博士生团队搞出双轴旋转式惯导系统,解决了漂移误差,精度全国第一,这成果让中国导弹、潜艇、卫星的导航又迈了一大步。 高伯龙把实验室当家,穿着朴素的背心,埋头实验台前,人称“背心院士”,他从不计较得失,只想让中国军事科技不受制于人。 1993年那台“罢工”的样机,最终被团队驯服,成了中国激光陀螺史的转折点,1999年,中国导弹开始装上他研发的激光陀螺,导航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信息来源 《永不停转的“陀螺”》 《高伯龙:奋斗40载成功研制激光陀螺》 《用生命转动“至强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