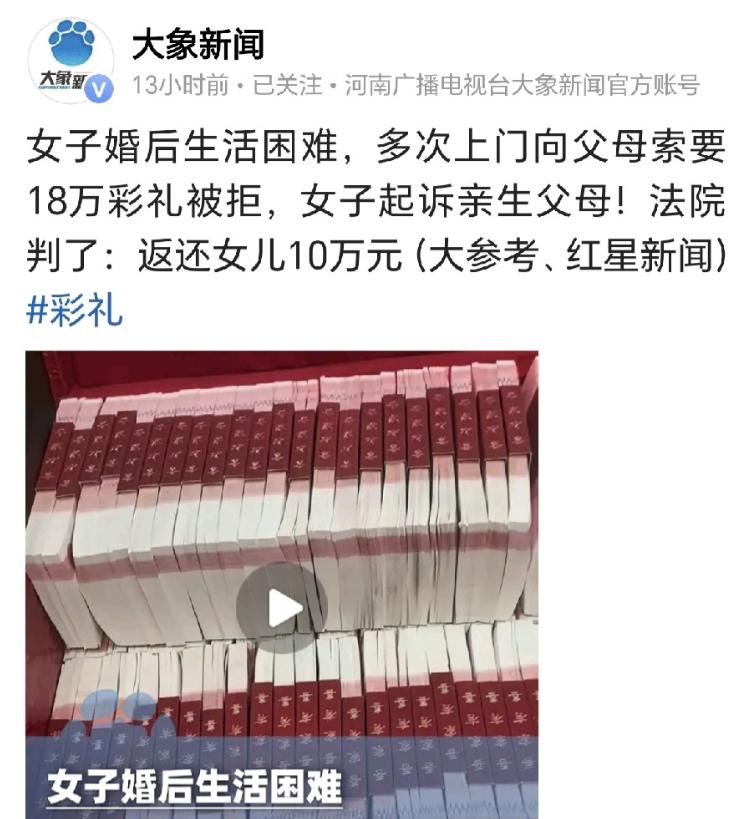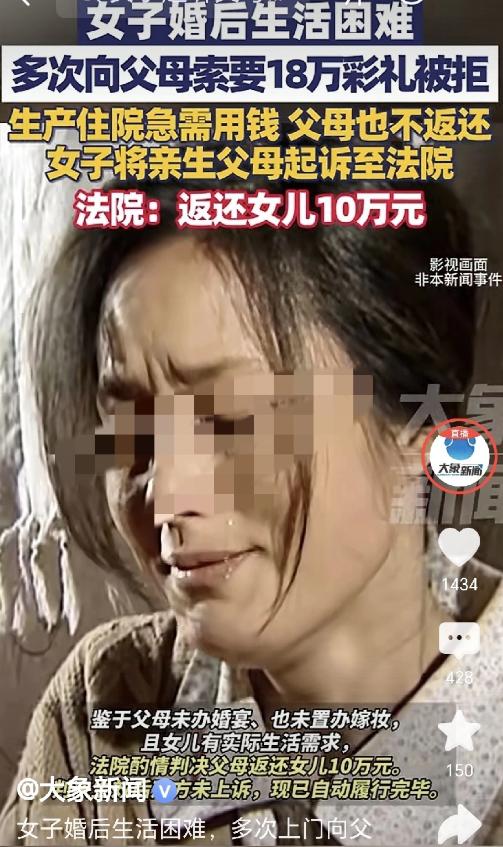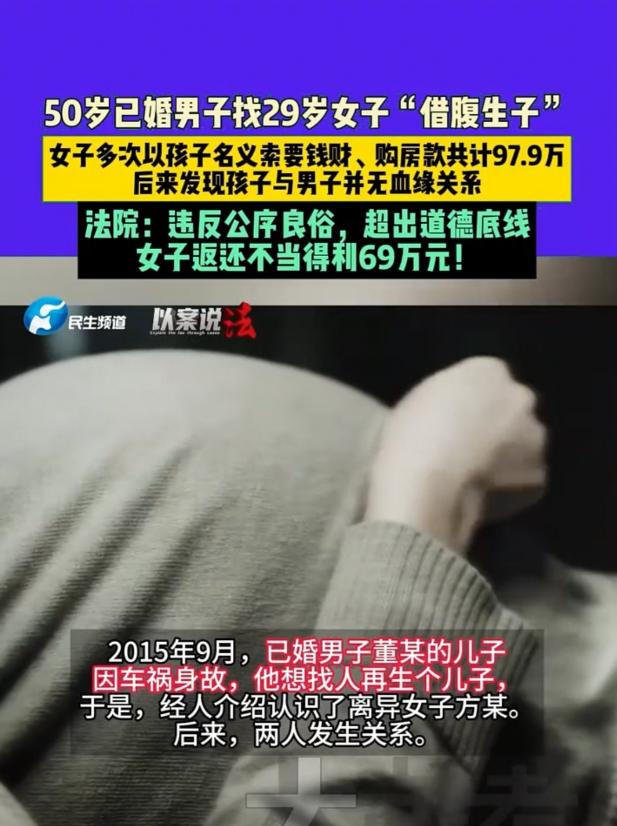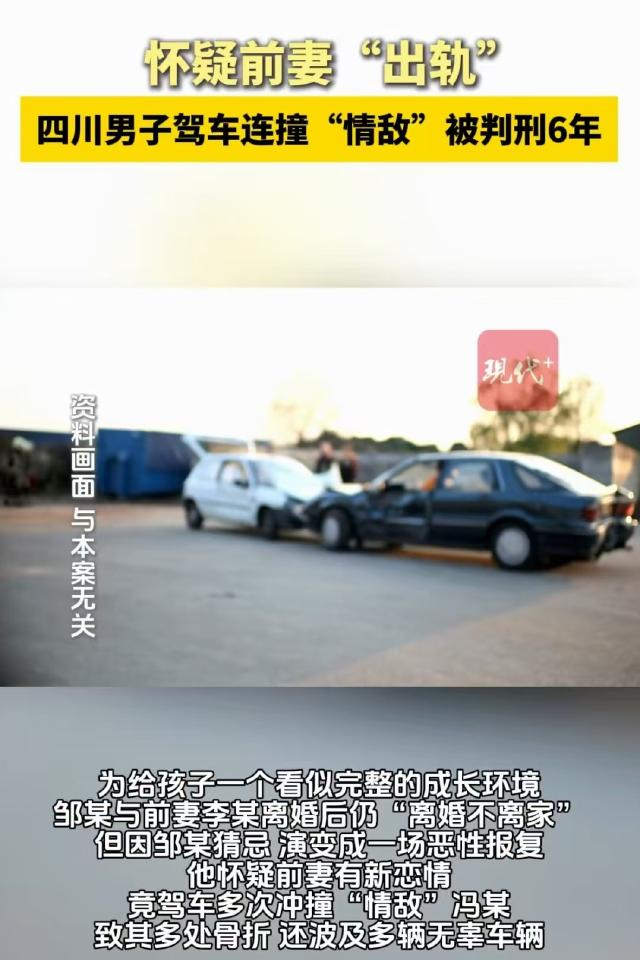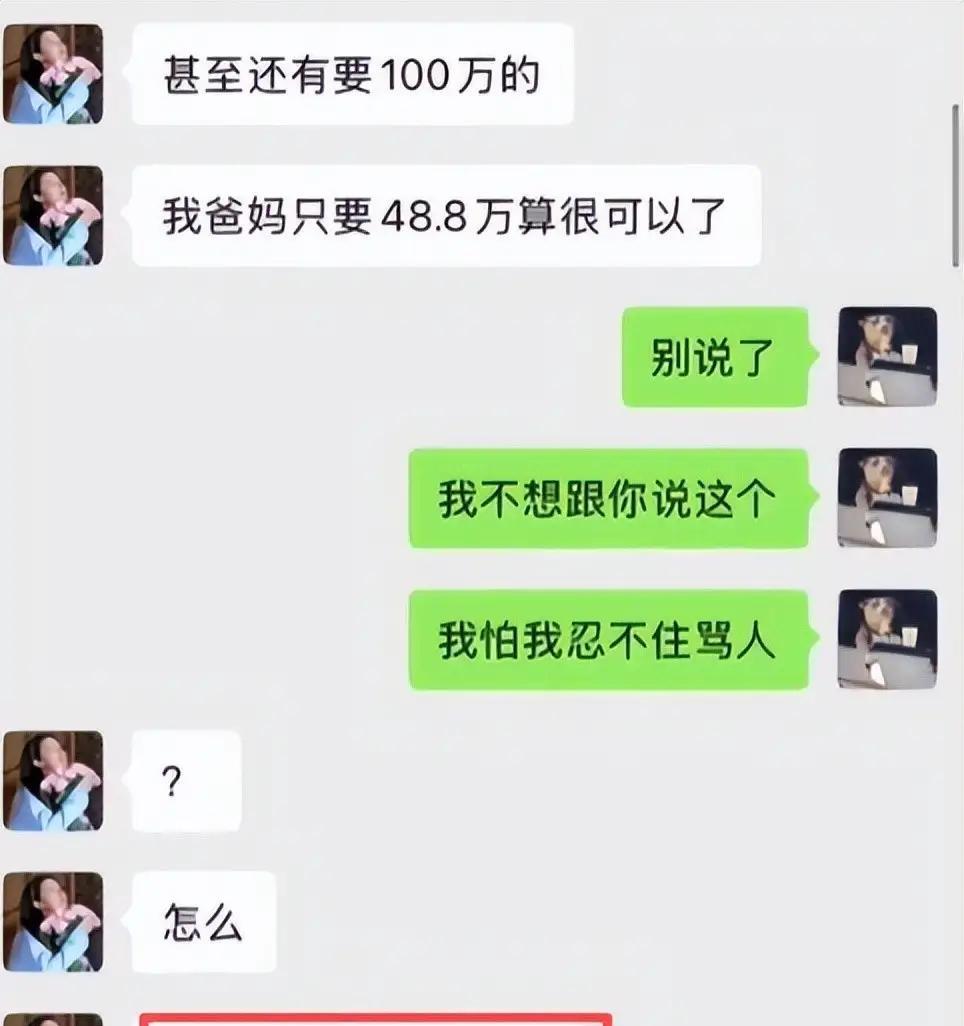浙江台州,女儿结婚,男方家庭依习俗支付了18万元彩礼,但父母收下后未置办一分钱嫁妆,反而全部留作己用。女儿婚后生活拮据,甚至怀孕生产时连医疗费都缴不起,求助父母却屡屡碰壁。直到她将父母告上法庭,事情才有了一个法律层面的答案。 张小某与林某相识于2020年,经人撮合后确定关系。按照当地习俗,林某家在定亲时交付180000元彩礼。这笔钱当时让张小某父母十分高兴,觉得男方“有诚意”。可婚事真正办下来,父母既未出资为女儿置办婚宴,也未准备嫁妆。张小某就这样空手嫁进林某家。 然而,婚后的日子并不如她所想。林某家为筹备彩礼早已掏空家底,家庭条件捉襟见肘。张小某嫁过去才几天,就感觉压力沉重。她想到,彩礼本该用于新家庭生活,于是返回娘家,向父母要求返还部分资金,哪怕拿出一部分来支撑日常开支。父母却拒绝,认为“彩礼是父母应得的”,甚至直言“养女儿这么多年,花费岂止18万”。 张小某一次次哀求,父母偶尔给她一些生活费,却坚决不肯动彩礼分文。直到她怀孕后,问题愈发突出。林某微薄的工资难以维持开支,更不要说支付生产费用。张小某在病床上抹着眼泪,打电话恳求父母:“我就要生了,住院费都交不起,你们能不能把钱还我一些?”父母仍旧冷漠,只在孩子出生时给了一个8800元红包,声称“算是尽了心意”。 彻底绝望的张小某,选择用法律途径维权。一纸诉状,她将父母告上了法院,要求返还18万元彩礼。 从法律层面来看,彩礼到底属于谁? 根据《民法典》第240条,所有权人对不动产或动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婚姻中的彩礼,本质上是基于缔结婚姻的目的,男方家庭向女方家庭支付的一种附条件的赠与。长期以来,社会上存在“彩礼归父母”的观念,但司法实践更加注重其“保障新婚家庭生活”的功能。 法院审理后认为,彩礼既不是父母的独享财产,也不是女儿个人完全独立的财产,而是基于婚姻习俗支付给女方家庭的共同共有财产。此案中,父母收下18万元,却未为女儿准备嫁妆,更未用于支持女儿的小家庭,显然违背了赠与的本意。 《民法典》第6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当女儿生活陷入困境,父母却一味坚守“彩礼是自己家的”,有违公平与家庭伦理。 此外,法院还援引了《民法典》第657条,赠与一旦成立,受赠人原则上有权使用,但若存在附条件或附义务的赠与,应根据实际履行情况判断归属。本案中,彩礼的合理用途应是支持张小某婚后的生活,而非被父母截留。 最终,法院酌情判决:父母应返还张小某10万元彩礼。虽然未全额返还,但考虑到父母对子女养育的付出,以及习俗上对父母的补偿,法院作出了折中裁定。 这个判决释放出三个关键信号: 第一,彩礼并非父母的专属利益。司法实践倾向于认定彩礼属于女方家庭共同财产,应合理用于女儿婚后生活。父母若截留,甚至导致女儿生活困境,可能构成侵权或不当得利。 第二,公平原则成为裁判核心。法院不会机械照搬传统习俗,而是结合家庭实际情况,平衡父母养育投入与子女婚后需求,作出符合社会正义的判断。 第三,亲情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在这起案件中,父母与女儿本该互相扶持,但因彩礼产生对立。法律的介入,不仅是对女儿权益的保障,更是对家庭伦理的提醒。 彩礼,本是中国传统婚俗的一部分,原意在于表达诚意、支持新家庭。然而在现代社会,它却常常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张小某的案例正是缩影:当彩礼被父母视为“回报”,忽略了女儿婚后的实际困难,亲情最终走向裂痕。 在法院判决后,张小某虽拿回部分钱款,但心理上的伤痛难以弥补。她曾说:“他们根本不管我死活,只看重钱。”这样的心酸,才是真正令人叹息的地方。 法律之外,这个案例更是一记警钟。父母对子女的养育付出无法用金钱衡量,但彩礼的意义,绝非变相索取“补偿”。在现代法律语境下,彩礼应服务于新家庭,而不是割裂亲情的工具。 当情与法交织,我们看到的结论是:彩礼归属的最终裁判,不是习俗,而是公平与理性。 这一纸判决提醒每个家庭:亲情应以关爱为本,法律则是最后的守护。若连女儿生产住院都得不到支持,父母执拗守住的钱,究竟还有多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