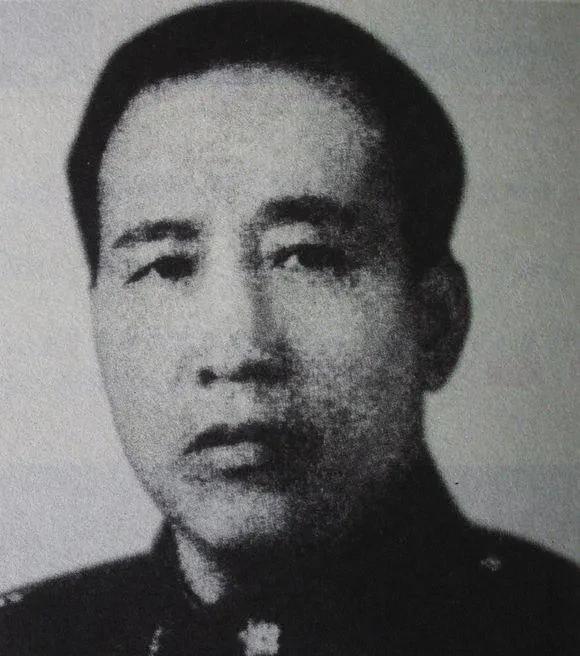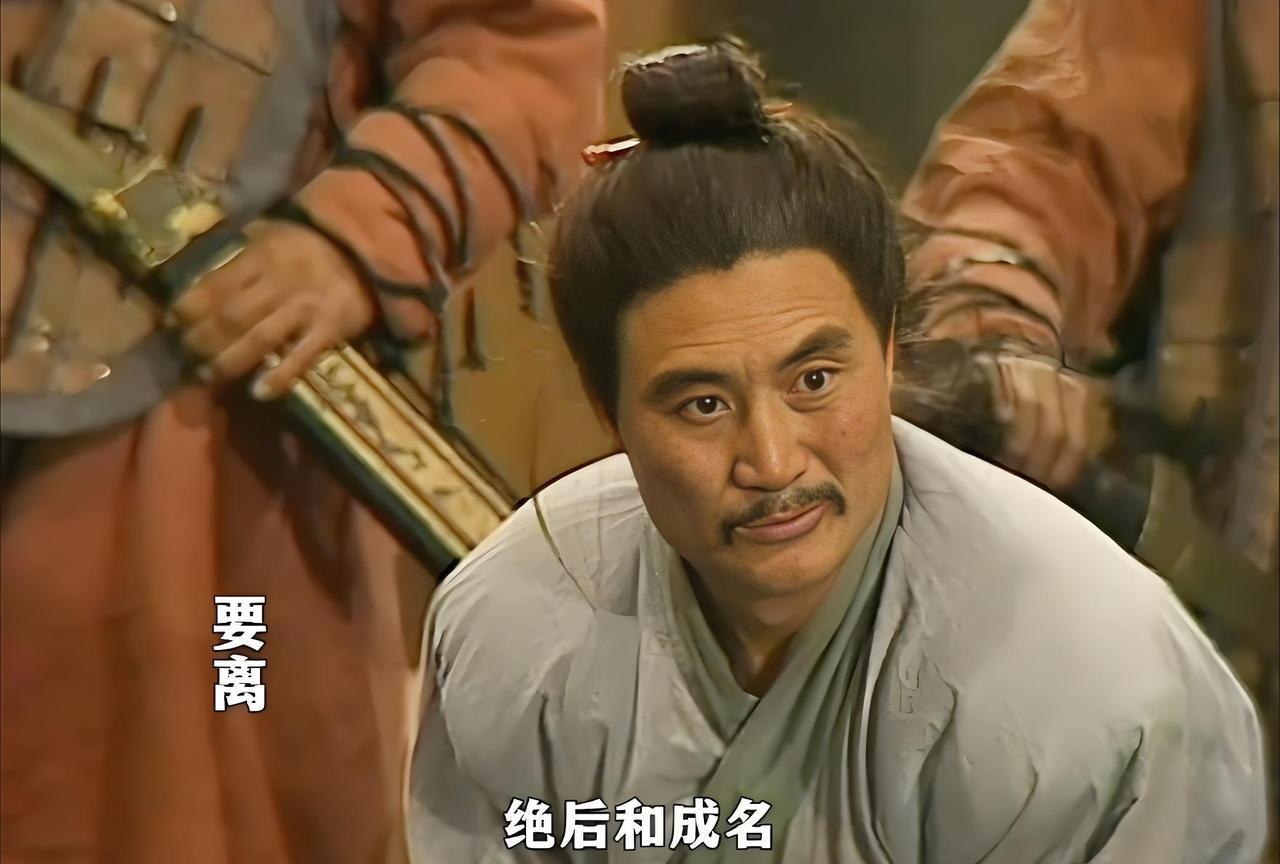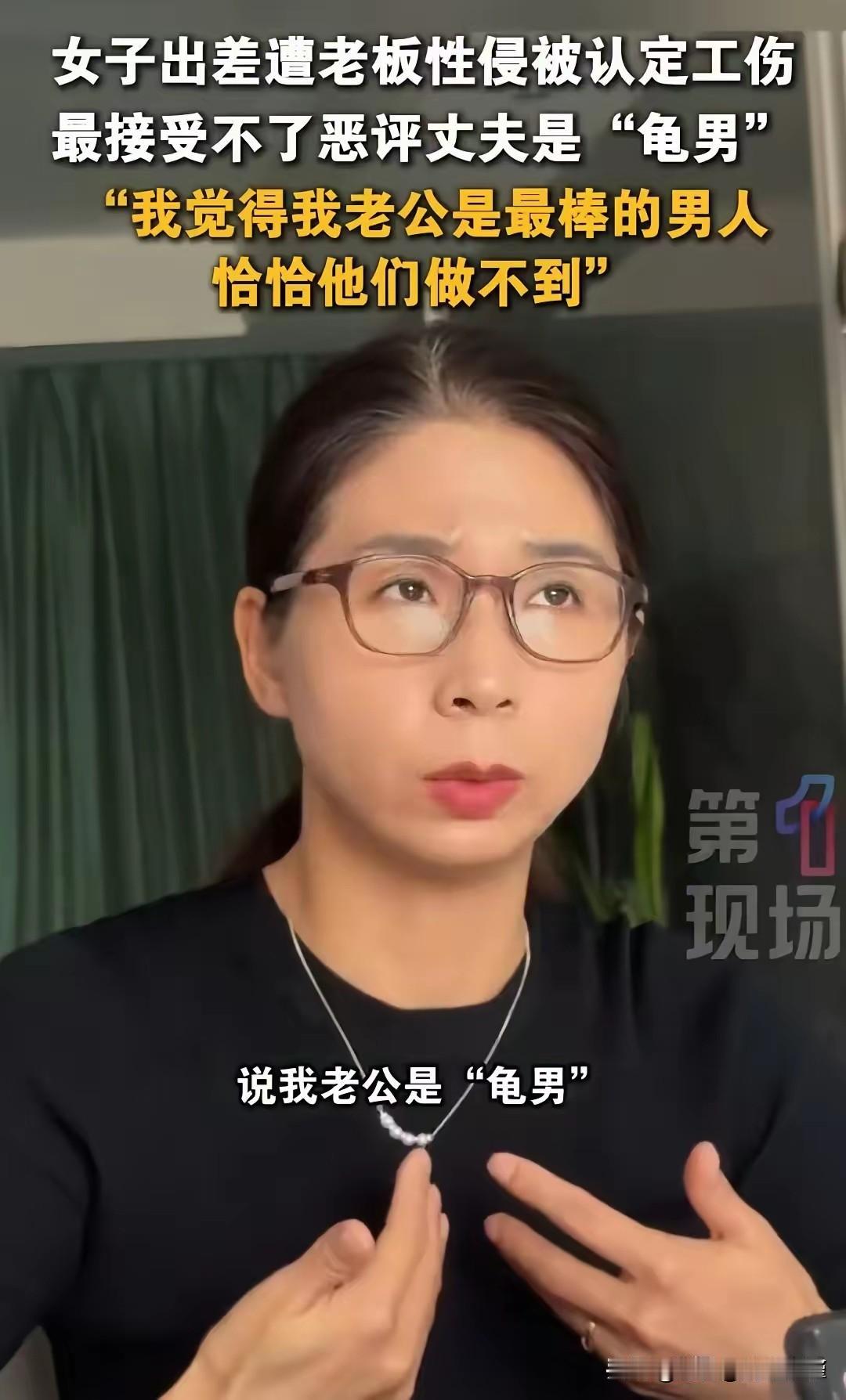他被留沈阳当警备师长,找陈奇涵要入关,追到部队平津战役结束了 “1948年11月3日凌晨,陈参谋长,我想跟着大队伍进关!”王兆相压低声音,却难掩急切。陈奇涵抬头看了他一眼,只回了两个字:“等批。” 一句“等批”让王兆相在沈阳又待了整整七十二小时。城市刚刚解放,焚毁的仓库还在冒烟,电车轨道上堆满了缴获的缴弹。沈阳需要秩序,需要一支熟悉城防的部队来稳住局面,因此警备师长的任命很顺理成章。可王兆相心里全是前线:东野十二个主力纵队浩浩荡荡踏上关内铁路,他的师却被按在原地,这滋味并不好受。 回溯到一个月前,他的独立十三师还在长春城外打“哑巴仗”。城里饿得骨瘦如柴的守军时而挥白旗,时而端上机关枪,前后反复。10月17日拂晓,青年军二〇七师趁夜摸索突围,结果撞上十三师预备队,短兵相接不到两小时,五百多人扔下武器。可没过多久,城内又传枪声,那支部队内部派系林立,一派要投降,一派要硬撑。王兆相干脆下令火力压制,才结束这场闹剧。 长春解放之后,东北野战军旋即南下,关键目标是沈阳。打沈阳时,十三师分到的任务是堵截机场与城东交通线,以免守军飞走或突围。任务不算露脸,但如果做不好,锦州、辽西两场胜利便可能被抹平,风险极大。王兆相带着十几门山炮苦熬两夜,挖暗道、埋炸药,最终在城东一线堵住了敌军逃路。沈阳守军的心理防线随之崩塌,主力纷纷弃械。战斗结束当天,他接到任命:留城担任警备师师长。 回望个人履历,这种调动并非第一次。1947年夏天,三战四平,他还是第六纵队十八师师长。那一仗,他带兵硬顶城北突围口,结果被误判“动作迟缓”。一纸电报,他被抽到辽吉军区当军分区司令,实际就是后方维持。那段日子他琢磨透了:前线立功快,后方熬人。也正因为这段经历,组建二线兵团时他主动请战,新生的独立十三师才有了一个善打硬仗的主官。 沈阳安定尚需时日,为什么他仍然想往关内跑?理由很实际。其一,平津是华北门户,一旦截住,华北剿匪基本收官,他不想错过;其二,老部下多数在十二纵,纵队缺谁都行,但缺师长不好。更关键的一点:二十年来,他已经把“打到底”写进骨子,突然叫停,心里发空。 陈奇涵理解他的脾气,向四野首长递了报告。11月6日深夜,批复终于到手:准予调动,与十二纵队会合。电报一到,他只用了三小时完成交接,把城防细则与警察局长核对完毕,连夜登车。沈阳到天津的铁路因为毁坏,需绕经锦州、山海关,再换津浦线,全程三十二小时。如果不是几处桥梁临时维修,他还要更快。 等火车在天津东站嘎然停下,平津战役的硝烟却已散去。19天的围困,傅作义部基本放下武器,塘沽一线还残留几股摩擦。十二纵队的番号已经写在接防令上:“接管塘沽海防,防止敌舰炮骚扰。”王兆相赶到指挥所,陈德一句玩笑:“老王,这次又慢半拍。”他没辩解,只盯着地图上往南延伸的箭头——那里还有中原、还有江南。 1949年初春,大规模整编展开,独立师序列被撤销,十三师划入四十七军,番号一变再变。新任务依旧是警备:留下天津,巩固华北。王兆相从小年守到正月十五,外地援兵与地方干部先后进入,秩序基本成型。榆木一样的性子又坐不住,他找到军里,提出“警备已稳,请求南下”。批文批得比上次快,三个小时后,他又在车站等待开往南方的列车。 河北、河南一路向南,车到光化,正碰上渡江战役准备阶段。江面炮火将至,每支部队都在抢时间。四十七军被列入第二梯队,任务是武汉、西陵线方向。王兆相终于赶上硬仗:咸宁、通城两线突击,山丘与丛林夹杂,难度不比东北平原的冬战低。六月初,湖南北大门被撬开,部队直逼衡阳。他的团以上干部伤亡三成,但推进速度全军第一,算是出了口气。 有意思的是,多年后谈及这段频繁的进退,他只总结了半句话:“听令行事,不挑活。”外人看来,三次被留守、两次追赶主力,既窝火又曲折;站在军队组织的逻辑里,却再正常不过: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调。遗憾的是,假如首发冲进平津,新中国军功簿上大约会多一笔“十三师攻城”,这想必也是他心底那个小小的不甘。 作战序列调整尘埃落定后,王兆相职务停在了军副参谋长。有人说他锋芒太露,也有人说他不懂官场。可熟悉的人清楚,六纵、辽吉、十三师一路走来,他最在乎的是“能用人”。东北老兵爱叫他“王愣子”,却都抢着跟他一个营。原因很朴素:仗打得实在,账算得明白。 顺带提一句,他的妻儿一直留在沈阳。当年他走得急,家中只留一句话:“等我胜利回家。”1950年冬,朝鲜战事刚刚告急,他又被点名抽调前指。临行前,老友开玩笑:“这下可别再追着大部队跑了。”王兆相没笑,提起行囊便上车——骨子里那股劲儿,从未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