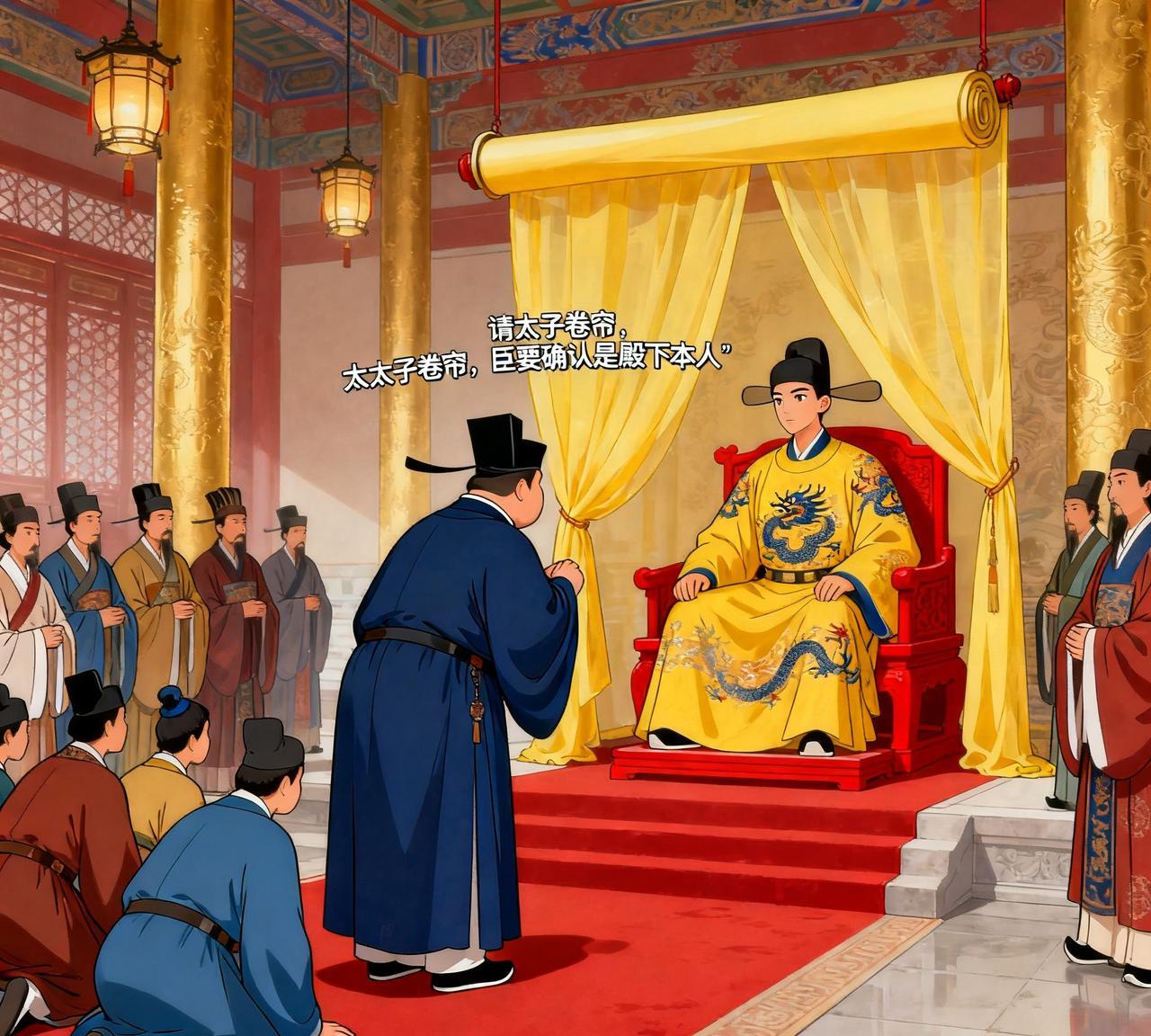1729年,养心殿的烛火彻夜通明。 52岁的雍正皇帝,刚从堆积如山的奏折中抬起头,眼中满是血丝。他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声音沙哑地对身边的太监说:“传吧。” 不多时,一个瘦弱的身影被一床锦被包裹着,像一件贡品,被抬到了龙榻之上。 她就是马氏,一个刚满13岁、入宫才三个月的女孩。她甚至连宫里的规矩都还没学全,就被推到了帝国权力的中心。 被子被掀开,冷气瞬间包裹了她。她赤裸着,蜷缩在巨大的龙床上,能清晰地听到殿外铜漏滴水的声响,一下,又一下,仿佛敲在她的心上。 殿内梨木的暖香混着皇帝常用的“四合如意香”,让她有些晕眩。 雍正帝带着一身疲惫走近,借着烛光打量着这个女孩。她脸上满是惊恐,稚气未脱,像一只受惊的小鹿。或许是在这张脸上看到了某个故人的影子,或许只是单纯地厌倦了宫中那些刻意的逢迎,他没有多余的话,只是躺下,疲惫地挥了挥手:“累了,安置吧。” 马氏僵在原地,准备了一路的江南小调、民间趣闻,全都堵在了嗓子眼。她不知所措,只能用细如蚊蚋的声音应了一声:“好。” 她不敢睡,也不敢动,就那么垂手站在床边,像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像。直到天快亮时,雍正翻了个身,半梦半醒间问了一句:“你叫什么?” “回……回皇上,奴才马氏。”她声音颤抖。 “马氏……”皇帝含混地念叨了一句,便再无声息。 她就这么站了一夜,直到晨曦微露。谁也想不到,第二天敬事房呈上绿头牌时,雍正那根批阅过无数生死的指头,径直点中了“马答应”。 从此,马氏的牌子仿佛被焊在了托盘上,日日被翻。她成了紫禁城里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她既不会唱曲,也不会下棋,更不敢对朝政指手画脚。每次侍寝,她都只是静静地坐在一旁的小杌子上,或者在皇帝睡着后安静地站着。 雍正处理政务时,她在;雍正因国事烦忧时,她在。她像一株无声的植物,不打扰,只陪伴。 对这位以勤政著称、内心高度紧张的皇帝来说,这份“清净”成了最难得的慰藉。雍正曾对她说:“宫里吵得慌,就你这儿清净。” 恩宠带来了地位的提升,她从“答应”晋为“常在”。虽然依旧位卑,但炭火的份例足了,身边的宫女太监也换上了谄媚的笑脸。 她天真地以为,只要这样安分守己,或许就能在这深宫里,安稳地过一辈子。 她不懂,帝王的恩宠,从来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仅仅在于他此刻需要什么。当他需要安静时,你是解语花;当他不再需要时,你便什么都不是。 转折发生在雍正八年(1730年)的初夏。 五月初四,一个消息如惊雷般炸响在紫禁城上空——皇帝最倚重、最疼爱的十三弟,怡亲王胤祥,薨了。 这位亲王是雍正帝“九子夺嫡”时最坚定的盟友,登基后最得力的臂膀,是他在这孤家寡人的皇位上,唯一的精神支柱。雍正的天,塌了。 他罢朝数日,亲自为弟弟撰写祭文,字字泣血。 史书记载,雍正“面浮咳血,昼夜需人扶坐”,精神与身体瞬间被击垮。太医院的药炉日夜不熄,滚烫的药汁续的是帝王的命,却也熬干了后宫所有女人的期盼。 整个皇宫被巨大的悲恸和压抑所笼罩,百日之内,不得有任何丝竹宴乐。后宫彻底变成了一座死气沉沉的冰窖。 马氏的世界,从那一刻起,被彻底按下了暂停键。皇帝沉浸在失去手足的剧痛和愈发繁重的政务中,再也想不起,在后宫的某个角落,还有一个姓马的常在。 她的绿头牌,被遗忘在敬事房的角落,落满了灰尘。 她从最初的翘首以盼,到后来的渐渐失望,再到最后的彻底绝望。日子一天天过去,她看着新入宫的秀女,比她更年轻,更得圣心,在短短时间内扶摇直上。 而她,永远地停留在了“常在”这个位分上,再未动过。 雍正十三年,在位仅十三年的雍正帝驾崩。年仅二十出头的马氏,和先帝的一众嫔妃被移居寿康宫,成了太妃。 她的人生,在最美好的年华,就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的三十多年,她像一道影子,活在紫禁城的角落里。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马常在薨逝,终年五十二岁。这位在雍正朝有过短暂荣光的女子,死后甚至没能被葬入雍正帝的泰陵妃园寝,那是属于皇帝妃嫔们最后的归宿。 根据清宫档案记载,她被孤零零地安葬在清东陵风水墙外的苏麻喇姑园寝。 这是一个专门埋葬康熙朝及以后低等嫔妃和格格的地方,生前卑微,死后亦然。 从十三岁入宫,到五十二岁离世,三十九年的宫廷岁月,马氏的一生就像那晚她应的那声“好”,顺从、卑微,最终悄无声息地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 她或许到死也不明白,那持续了近一年的恩宠,究竟是为何而来,又为何而去。 她只是帝国运转中一颗微不足道的螺丝钉,被需要时拧紧,被遗忘时生锈,如此而已。




![乾隆真是职业皇帝名不虚传[吃瓜]](http://image.uczzd.cn/5141156089266685545.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