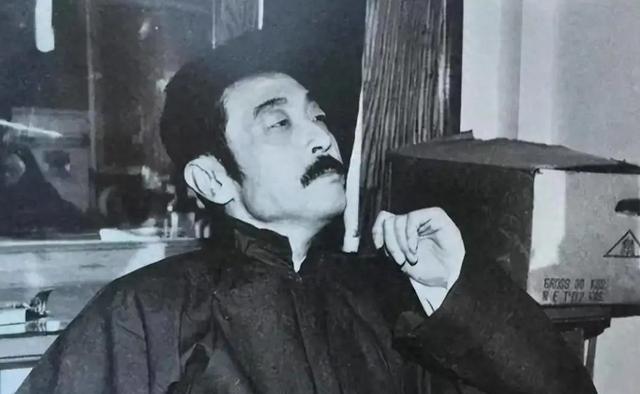世人皆知鲁迅本名周树人,却不知周树人,原来是周总理的叔叔 鲁迅是浙江绍兴人,这我们都知道。周总理呢,出生在江苏淮安,但他的祖籍也是浙江绍兴。老话讲,一笔写不出两个“周”字,他们二位,还真是正儿八经的同宗同族。 根据族谱考证,鲁迅和周总理的共同祖先,可以追溯到宋代的著名理学家,写《爱莲说》的那位周敦颐。往下排,鲁迅是周敦颐的第三十二代孙,而周恩来是第三十三代孙。这辈分一出来,不就清楚了吗?鲁迅,确实比周总理大一辈。 周总理对这件事非常看重。1952年,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去中南海做客,总理一见她,就非常认真地说:“排起辈分来,我应该叫你婶母哩。”许广平当时自然是连连说不敢当。 又有一次,是1969年,总理在开会期间,专门去北京饭店看望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他操着一口绍兴乡音,亲切地对周建人说:“建老,我已查过哉,你是我的长辈,我要叫你叔叔。”你看,这话说得多么恳切和自然。 聊到这,你可能会想,既然是亲戚,那他们生前肯定见过面,关系不错吧? 这恰恰是历史最有意思的地方——他俩,一生都未曾谋面。 本来,他们有过一次绝佳的见面机会。那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潮正劲。21岁的周恩来在天津组织了进步社团“觉悟社”,搞得有声有色。他们当时计划邀请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来演讲,名单上就有鲁迅。 时间都定好了,是1919年11月8日。天津的青年们翘首以盼,周恩来更是充满了期待。可偏偏就在那天,鲁迅先生临时有事,去不了了。先生刚在北京的八道湾买了套房子,正忙着盯装修、付工钱呢。 鲁迅日记里记得清清楚楚:“八日晴。下午付木工泉五十。”就是这件“家务事”,让他错过了与那位“侄儿”的相见。最后,只好由他的弟弟周作人代他去了天津。 这件事,周总理一直记在心里,觉得非常遗憾。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1971年,他在接见一位日本的鲁迅研究专家时,还提起了这段往事,言语间满是惋惜。 一次擦肩,就是一生。命运的安排,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但这并没有阻碍两位伟人之间的“神交”。 虽然没见过面,但周总理对这位“本家大叔”的敬佩和关心,是实打实的。上世纪20年代末,上海的“革命文学”论争闹得不可开交,一些左翼作家把矛头对准了鲁迅。当时,在中央领导核心工作的周恩来敏锐地察觉到这个问题,他明确指示,要立刻停止对鲁迅的攻击,要团结他、争取他。 他曾动情地说:“一句话,今后党在文艺战线上的旗帜是鲁迅。”这份信任和支持,在当时的环境下,对鲁迅来说是何等珍贵。 鲁迅先生那边呢?他对这位未曾谋面的“侄儿”,同样怀有好感。1936年,就在鲁迅去世前不久,他特意准备了两本刚刚出版的《海上述林》,托冯雪峰转交到陕北。他还特别叮嘱,一本皮脊的送给毛主席,另一本蓝绒面的送给周总理。 一个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一个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领导革命,素未谋面,心中却都惦念着彼此。 鲁迅先生逝世后,周总理更是用一生的时间,来纪念和弘扬这位“叔叔”的精神。 1938年,在武汉的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周总理开篇就说:“在血统上我也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他号召大家学习鲁迅“为真理正义而倔强奋斗,至死不屈”的精神,来坚持抗战。 1946年,在上海的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他再次引用鲁迅的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说,这就是鲁迅的方向,也是我们的立场。对敌人要横眉冷对,对人民要做孺子牛。这几句话,后来也成了周总理自己一生的写照。 他不仅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的办公室书架上,就常年放着一套《鲁迅全集》,他时常翻阅。1955年,他亲自去参观北京的鲁迅故居。那是个很小的院子,陈设极其简朴。 当他走到后院,他轻声问道:“鲁迅《秋夜》里的后园就是这里吗?那两株枣树在哪儿呢?”当听说原来的枣树已经枯死,现在的是后来补种的,总理的脸上流露出深深的惋惜。他对鲁迅作品的熟悉,对先生生活细节的关心,让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更有意思的是,当工作人员介绍鲁迅母亲安排的“爱人”朱安住的房间时,周总理爽朗地大笑起来,说:“咳,那怎么能叫爱人呢!”这一笑,充满了理解和人情味,瞬间拉近了伟人与我们普通人的距离。 这份敬重,甚至体现在了国家外交的最高舞台上。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那次“破冰之旅”震惊了世界。周总理为尼克松准备的国礼中,就有一套精装的《鲁迅全集》。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文化脊梁。 从宗族血脉上的叔侄,到革命道路上的神交,再到身后名节的守护。周恩来与鲁迅,这两位姓周的绍兴同乡,他们的人生轨迹虽然没有交汇,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却始终紧密相连。 周总理敬重的,不仅仅是那位血缘上的“叔叔”,更是鲁迅身上那种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硬骨头”精神,那种“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