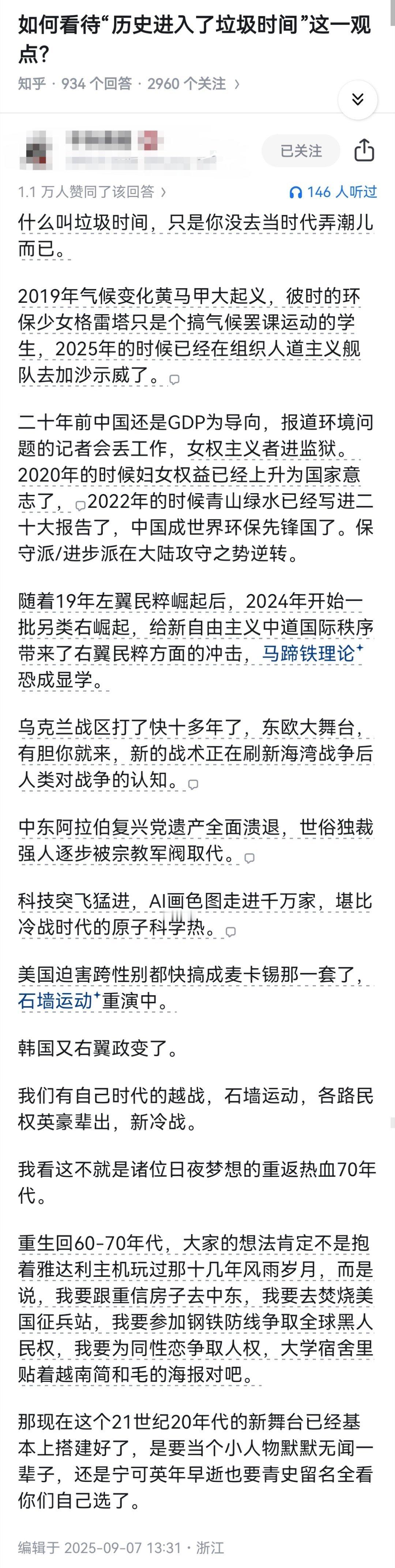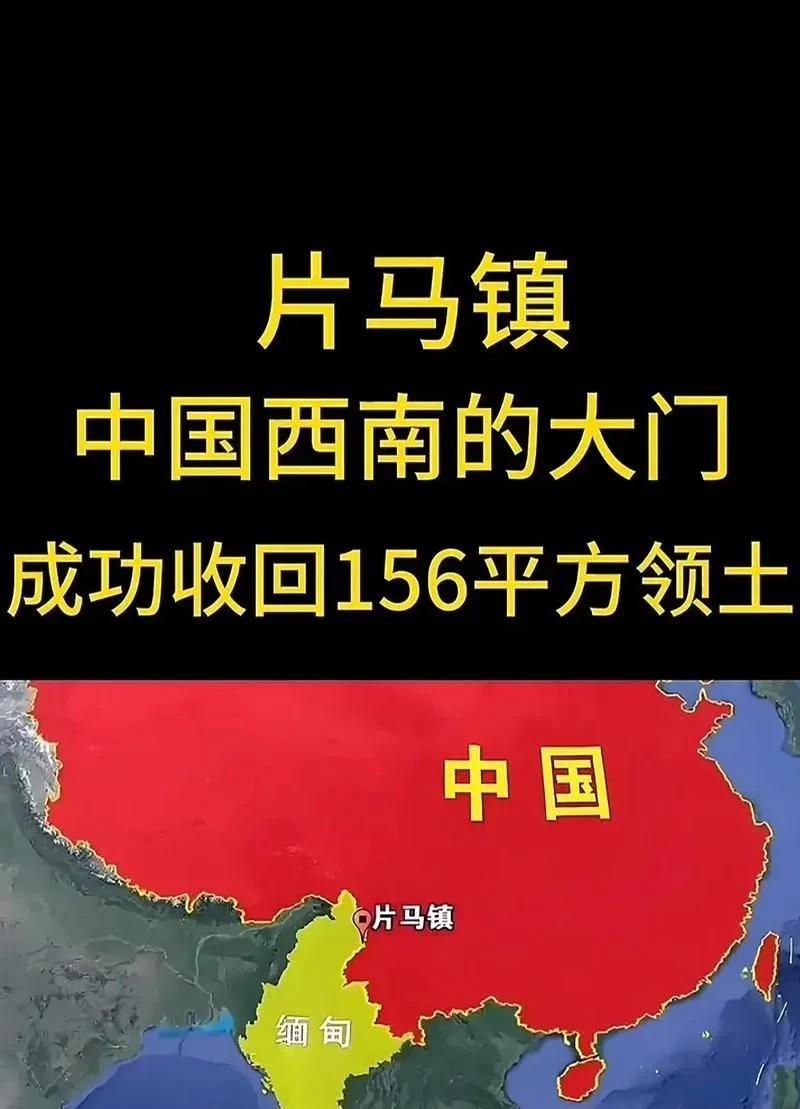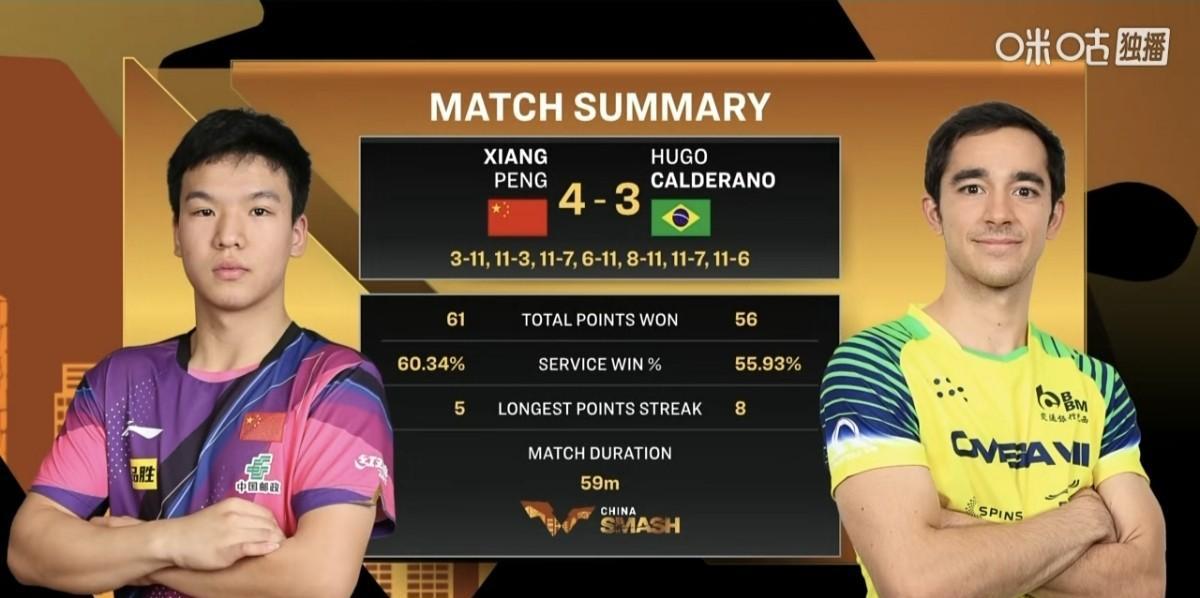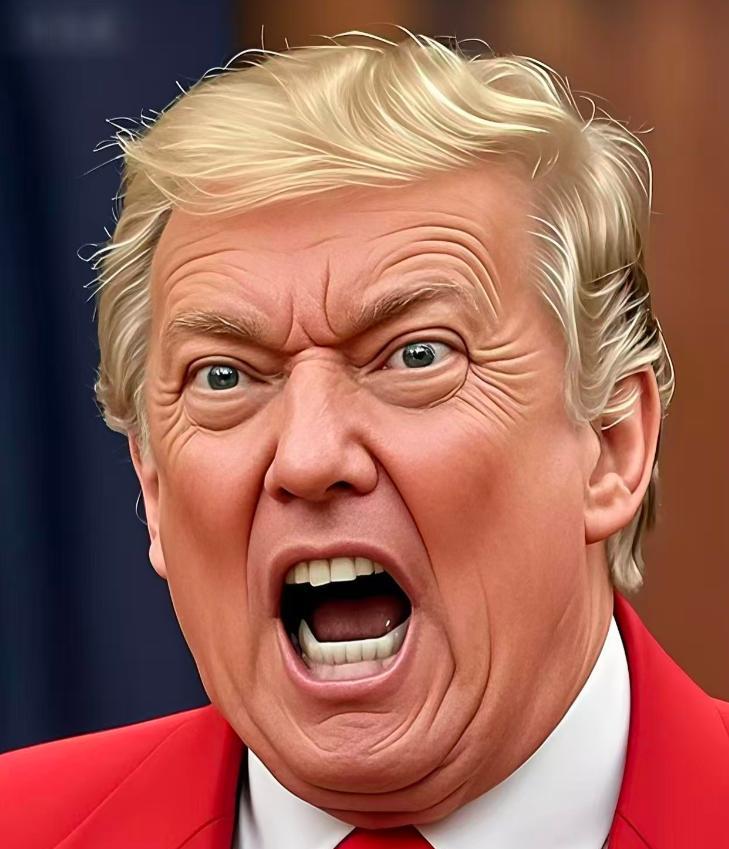1724年冬天,前朝废太子胤礽病入膏肓,他托人向雍正帝带话:“皇上,我是大不孝的罪人,按说您登基后若是想杀我,我绝活不到今天,可是承蒙您的关照,我这两年过得还不错,我很感激。谢谢了,老四。”胤礽临终前的这番话,带着几分释然,几分感激,还有几分无奈 养心殿里,雍正站在窗户前看着一份奏折。 这是废太子胤礽咽气前托人递来的口信:“皇上,我是大不孝的罪人,承蒙关照,我过得不错,谢了,老四。” 这一年,五十三岁的雍正已在龙椅上坐满三年。 胤礽与雍正的羁绊,要从康熙朝说起。 胤礽生而贵为嫡子,两岁被立太子,自小养在康熙身边,学的是帝王之术,交的是天下才俊。 那时的雍正不过是四阿哥,生母地位不高,在诸皇子中毫不起眼。 少年时的胤礽,曾是他灰暗岁月里的一束光。 有年冬日,小胤禛在御花园玩雪摔进冰坑,还是比他大十岁的胤礽跳下来将他救出。 还讲自己的暖手炉给了他:“老四身子弱,仔细冻出病来。” 那时两人情同手足,谁能想到后来这对兄弟会走到兵戈相向的地步? 变故起于康熙四十七年。 太子首次被废,罪名是“不法祖德,不遵朕训”。 胤礽被圈进咸安宫,从前锦衣玉食的储君,一夜之间成了阶下囚。 雍正那时已成年,曾去探望过一次。 铁栏后的胤礽头发花白:“你最会装!当年我何等照拂你,如今倒成了踩着我的梯子上位的人!” 骂声里的委屈,雍正不是不懂。 康熙晚年,九子夺嫡搅和着朝局混荡。 大阿哥魇镇太子,三阿哥暗中结党,八阿哥胤禩广结人心被称作“八贤王”,连十四阿哥都成了他最有力的竞争者。 胤礽两度被废,表面是触怒康熙,实则是储位之争的总爆发。 雍正最终胜出,靠的不是喊口号,是在康熙面前始终保持着“诚孝”的姿态。 雍正元年,他坐在太和殿接受百官朝贺时,胤礽正在景山的圈禁所里啃冷馒头。 按常理,废太子是颗定时炸弹。 他曾是合法储君,余党未消,可杀了他,又落个“弑兄逼父”的骂名。 雍正的选择出人意料。 他不杀,反而给胤礽换了更宽敞的宅院,按月送米送炭,甚至派太医定期诊脉。 大臣们背后议论:“皇上这是收买人心?” 只有雍正自己清楚,他要的不是“收买”,是“止血”。 登基头两年,他的日子比当皇子时还累。 老八胤禩封了廉亲王,却总在朝会上阴阳怪气。 老九胤禟在外头散布“雍正得位不正”,老十胤䄉抗旨不去张家口,最头疼的是老十四胤禵,康熙丧期时当众质疑他的继位资格。 雍正没急着动手,因为他知道不能着急。 他一面提拔十三阿哥胤祥,把户部、兵部的大事都交给他,有了这个“铁杆兄弟”撑腰,朝局渐渐稳了。 一面拿老八开刀。 先封他虚职架空权力,再借“结党营私”的罪名削其爵位,最后圈禁至死。 老九更惨,被抄家后发往西北,连名字都被改成“塞思黑”。 可轮到胤礽,他的刀始终悬而不落。 有人劝他:“废太子留着终是祸患。” 他只说:“我当年落难时,他给过我暖手炉。” 话是真,理却不全。 说白了,他只是不想再看到“兄弟相残”的局面再次出现。 1724年,胤礽病了。 太医诊出是肺痨,没几年了。 雍正听说后,没按规矩让内务府随便应付,特意把自己喝的人参阿胶拨了一匣子过去。 送东西的小太监回来禀报:“王爷喝了口参汤,笑着说‘皇上费心’。” 到了冬天,胤礽油尽灯枯。 弥留之际,他攥着康熙当年赐的玉如意,嘴里念叨着“阿玛”“太子妃”,最后喊了“老四”二字。 消息传到养心殿时,雍正正批着河南水患的折子。 出殡那天,他没去送葬,却顶着雪出了宫。 大臣们拦着说“龙体为重”,他挥挥手:“去看看吧。” 他站在雪地里,看送葬队伍慢慢消失在巷口。 这一年,胤礽五十一岁,比他小九岁,却先一步走了。 胤礽死后,雍正追封他为“理亲王”,谥号“密”。 朝野议论纷纷,有人说是“圣德”,有人说是“作秀”。 但只有局内人明白,这口棺材,合上了康熙朝最后一桩旧怨。 此后,再没人敢拿“废太子”做文章。 而雍正的新政也在一路推进,摊丁入亩减轻了百姓负担,火耗归公充盈了国库,整顿吏治让官员们不敢再明目张胆贪腐。 老十三胤祥成了他的左膀右臂,带着新政的春风刮遍大江南北。 主要信源:(北京日报客户端——张彧:关于雍正的历史谜团,这本传记的看法让人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