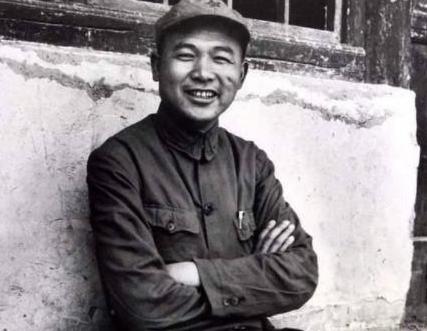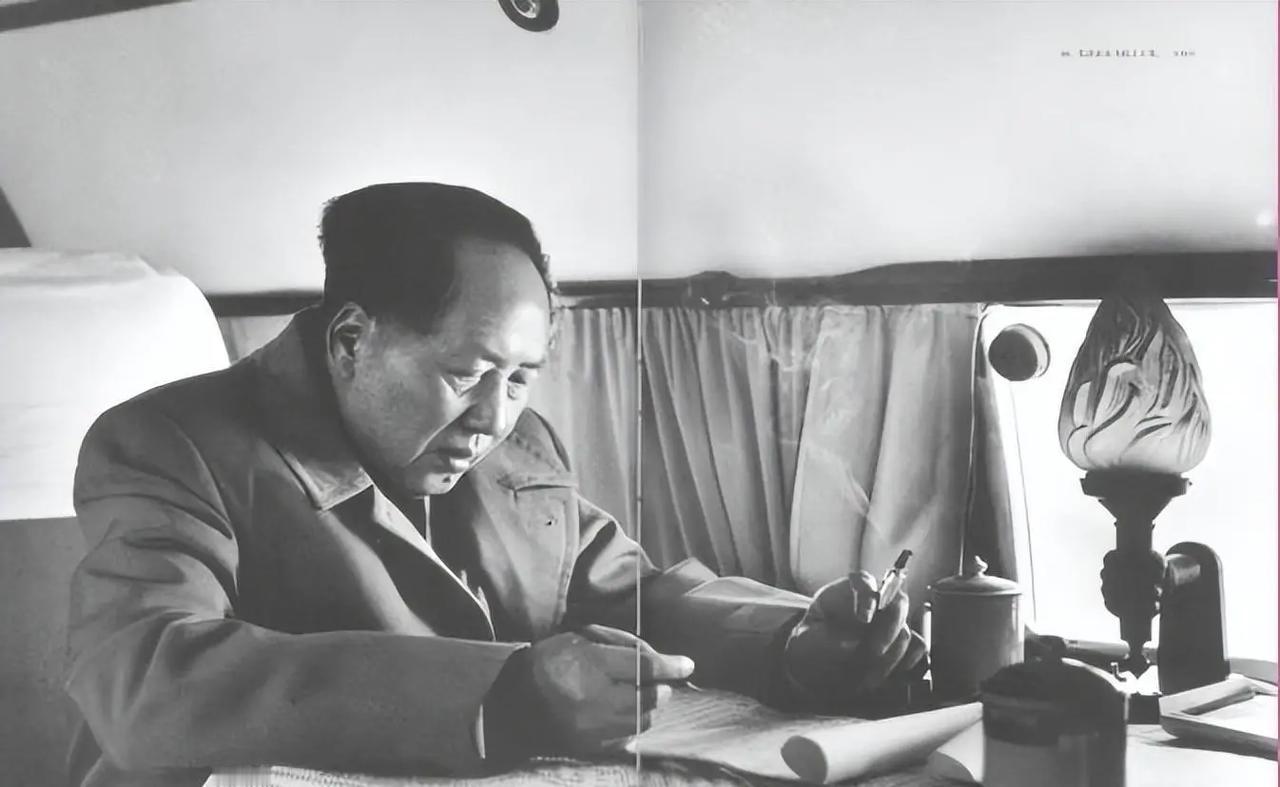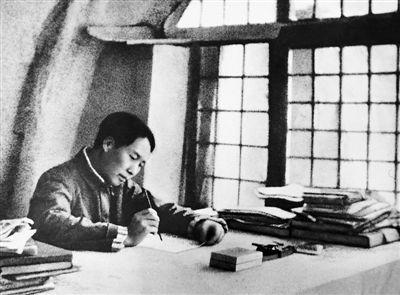“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前夕,毛主席拿着名单闷闷不乐,脸色阴沉地说道。原来是徐海东没能当选九大代表,毛主席为此深感不悦。 为什么徐海东没能当选“九大”代表? 很简单,身体原因。徐海东早在抗战时期就积劳成疾,得了严重的肺病,常年病榻缠绵,人根本不在北京。他本人也知道自己的情况,觉得不参会也无碍大局。但毛主席不这么想。对毛主席来说,徐海东这个名字,代表着一段不能忘记的历史,更代表着一种“不可藐视的革命力量”。 在中共历史上,徐海东和他的红二十五军那真是出了名的“能打、可靠”。长征路上,红二十五军是唯一一支在红军三大主力之外,能够单独行动并坚持下来的队伍,一路浴血奋战,最终到达陕北,为中央红军落脚提供了极大的战略支持。毛主席后来曾评价说:“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你们算第一。” 这份情谊,这份信任,早就超越了简单的上下级关系。 所以,当看到名单上没有徐海东的名字时,毛主席的心情一下子就到了谷底。他不是在纠结于一个名额,他是在担心,担心革命的火种,担心那些为革命流血牺牲的老同志,会不会被时代的喧嚣所遗忘。他要表达的是一种态度:革命的胜利,不是少数人的“清一色”,而是无数英雄儿女共同的付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些“打江山的人”。 毛主席对徐海东的这份执着,让我想起在创建新中国时,他对待“统一战线”的深刻思考。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面对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的问题,毛主席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平和好”。 当时,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刘斐代表国民党到北平谈判失败后,内心纠结是去是留。一次宴会上,他试探性地问毛主席:“打麻将是清一色好还是平和好?”毛主席笑着答道:“清一色难和,还是平和好。” “清一色”,就是一切由共产党一党专政;“平和”,就是多方合作,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刘斐豁然开朗:“平和好,那么还有我一份。” 毛主席反对“清一色”,不是出于客套或权宜之计,而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洞察和对民主政治的理解。他曾说:“真理不在乎是不是清一色。” 如果只依靠一小部分人,革命的基础是脆弱的。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两头小中间大”的,只有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都团结起来,才能把新中国建设好。 这种“平和”的思想,最终奠定了新中国最基本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徐海东的席位,代表的不是他个人,而是千千万万在革命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劳苦大众和忠诚将士。 其实,这种对“少数派”和“非核心力量”的尊重,在建国初期就体现得淋漓尽致。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民主党派觉得“历史使命完成了”,有的甚至准备解散。当时中央紧急叫停。毛主席明确指出:民主党派不能解散,不但要继续存在,而且要继续发展。他曾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来阐述其重要性: 认为民主党派是“一根头发的功劳”,一根头发拔去拔不去都一样的说法是不对的。从他们背后联系的人们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不可藐视。 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人民政协完成了“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历史使命。那么,政协还要不要保留?民主党派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答案是肯定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为了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继续保留人民政协。这项决策的政治学意义,在于破解了选举民主难以保护少数人民主权利的难题。在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基数巨大的国家,如果凡事只按简单的“人头数”投票,很容易忽略少数人的利益和声音。 而人民政协,正是通过“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这两种职能,让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民主党派人士等“少数派”拥有了发声的平台,确保了“多数尊重、少数兼顾”的中国式民主。 从这个角度看,徐海东的“席位”,和民主党派的“一把头发”,本质上是同一种政治关怀。他们是革命的“绿叶”,是社会的“少数派”,但他们的存在,是整个政治生命力旺盛的标志。 曾几何时,在一些人眼里,政协是“不打粮食”的闲职衙门。但近年来,随着“参政议政”职能的增加,以及“双周协商座谈会”等一系列制度创新,人民政协已经成为“凝心聚力第一线、决策咨询第一线、协商民主第一线、国家治理第一线”。 在国家重大工程的决策过程中,人民政协的声音甚至可以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 中共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不是简单压制,而是组织专家重新论证。正如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政协副主席钱正英所说:“正是不同意见才促进了三峡工程论证的深入。” 最终,1992年全国人大通过决议,代表们的掌声,既是送给支持者的,也是送给“反对者”的,因为他们都是“贡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