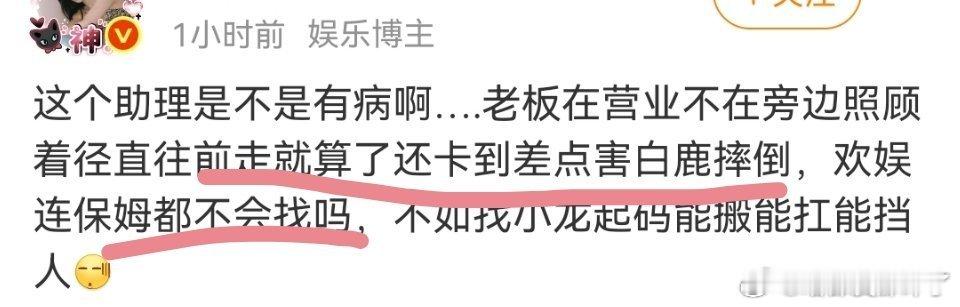我在新疆部队时,家属院分房时,一个小院因曾有一家属病死在那,多年没人愿意住。但因住房太紧张,一位正连军官急用房,就派人全面收拾好后住了进去,一住就是 10 多年。 这位军官姓王,战友们都叫他老王。那年他爱人刚怀上孩子,部队里带院的房子本就稀缺,即便听说院子的过往,他也没皱一下眉。收拾院子那天,几个战士帮忙扫落叶、刷墙,有个新兵蹲在墙根铲土时小声念叨:“连长,这土要不换换?老人们说……” 老王正搬着木柜往院里走,闻言放下柜子拍了拍新兵后背:“边疆的风都吹不散活人味儿,哪来那么多虚头巴脑的?咱们扛枪的,枪子儿都不怕,还怕这点念想?” 住进去第三年的冬天,雪下得特别大。老王爱人早起开门,发现院儿里的路扫得干干净净,雪堆旁还站着三个小雪人,每个雪人的“手”里都握着根小树枝——像极了边防岗哨的姿势。她愣在门口,想起昨夜老王值班没回家,家属院的人都知道她怀着孕,谁会半夜来扫雪? 这事过去没几天,家属院的张嫂子来串门,嗑着瓜子就扯高了嗓门:“妹子,你可当心点!前几年住这儿的那家,就是大冬天没的!” 老王爱人正揉着孕吐后的胸口,手里的毛线针“当啷”掉在地上。等老王晚上回来,她红着眼圈说想搬去集体宿舍,老王没说话,只是拉着她走到院角的老榆树下,指着树干上的刻痕:“你看,这是上个月你够不着晾衣绳,我刻的记号——要是真有啥不好的,它能让我安安稳稳给你刻记号?” 那些夜里的“沙沙”声,其实从住进来第一个月就有了。老王起夜时听见院儿里响,以为是风吹树叶,直到第二天看见老榆树下落了厚厚一层榆钱儿——明明还没到榆钱儿成熟的季节,倒像是有人特意摇下来的。当时他没多想,只当是天气反常,直到爱人遇见那件事。 那天老王爱人孕吐得厉害,半夜渴醒想找水喝,刚坐起来就看见房门“吱呀”开了条缝。一个穿蓝布衫的老太太端着搪瓷碗走进来,碗里是冒着热气的小米粥:“姑娘,喝口粥压一压。” 她吓得浑身僵硬,等反应过来要喊人,老太太已经没影了,可桌上的粥还是热的,碗边还沾着几粒没淘干净的小米。 老王第二天请假回来,拿着搪瓷碗问遍了家属院的老人。最东头的李大爷摸了摸碗沿,叹了口气:“这是老陈家的碗。老陈爱人走之前,天天给值班的战士送热粥,谁家有难处她都往前凑——她走那年冬天,雪下得跟今年一样大。” 老王爱人这才明白,那些扫干净的雪路、提前落下的榆钱儿,哪是什么怪事?不过是一个放心不下的老人,还在照着老习惯疼惜院里人。 打那以后,小院里的“巧合”更多了。晾在院里的床单被风吹落,回头就发现叠得整整齐齐放在石桌上;老王儿子出生那天,难产折腾了半夜,家属院的灯都灭了,只有他家窗台上的煤油灯——明明早就没油了——亮了一整夜。满月酒上,院儿里的向日葵突然“哗啦”响成一片,一只麻雀叼着颗瓜子落在孩子摇篮边,老王笑着举杯:“陈阿姨,谢您来喝喜酒!” 五年后部队分新家属楼,比小院宽敞亮堂,战友们都劝老王搬,他却守着老榆树不肯走:“这儿暖和,陈阿姨还没喝够咱娃的满月酒呢。” 有次卫生评比,战士们要把老榆树下的土挖掉换新的,老王急忙拦住:“这土是陈阿姨踩过的,换了她上哪儿找咱去?” 又过了十年,老王转业回内地。搬家那天,院里的向日葵开得正盛,金灿灿的花盘都朝着门口。他抱着已经懂事的儿子,指着老榆树说:“记住了,以后回来,得先跟陈奶奶问好。” 刚要上车,儿子突然指着院角石桌喊:“爸!那是什么?” 石桌上放着个蓝布包,打开是几双虎头鞋,针脚密得能数清,鞋面上的老虎眼睛——用的是院里红月季的花瓣染的布。 后来老王回新疆办事,特意绕到家属院。小院已经分给了个新军官,他站在墙外往里看,向日葵又长起来了,一个穿蓝布衫的老太太正帮着新军官的爱人抱孩子,衣角在风里飘着,跟当年他爱人看见的一模一样。新军官看见他,笑着招手:“王哥进来坐!这院儿邪乎得很——夜里总有人帮着收衣裳,今早我爱人还说,灶台上多了碗热粥呢!” 墙根的老榆树沙沙响着,像是有人在笑。老王摸了摸眼角,想起刚住进来时那个新兵的话——有些地方之所以让人安心,从来不是因为没有故事,而是因为故事里的人,把善意种成了比向日葵更长久的东西。那些被叫做“怪事”的,不过是一个好人,在自己熟悉的地方,继续做着熟悉的事罢了。
我在新疆部队时,家属院分房时,一个小院因曾有一家属病死在那,多年没人愿意住。但因
小依自强不息
2025-12-18 16:22:12
0
阅读: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