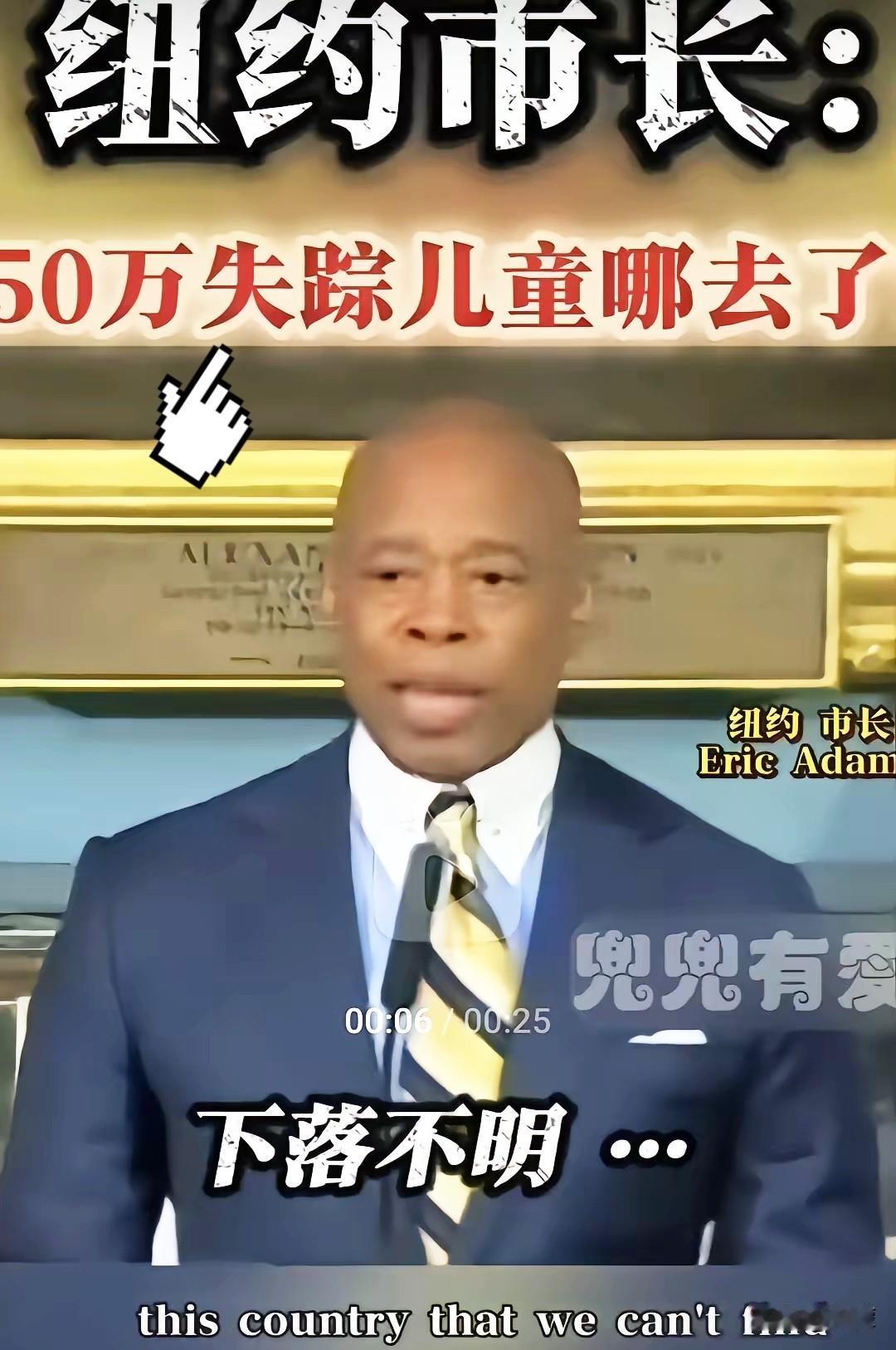62岁张财主,娶了19岁的小媳妇月红,一天晚上完事后,张财主摸着她的头发说:我这身子骨不济了,要是哪天走了,你得在祠堂里替我守满三年。 她本该在田埂上追蝴蝶,却被爹娘用十两银子卖进青砖黛瓦的大院。张家宅子看着体面,于她不过是一座镀金的牢笼。现在好不容易守完婚礼,接着就要进祠堂对着木牌熬三年,她知道,那跟活埋差不多。 早在几个月前,她就听管家提起“守祠堂的规矩”,那一刻,她熄灭了对婚姻最后一点期望。爹娘收了聘礼,族里只认张家脸面,没有人会替她说一句话。 后院晒被子的午后,翠儿在她耳边说起镇上的戏班,班里有个青衣原本是大户少奶奶,跑出来唱戏,如今活得自在。那一瞬,月红第一次知道,女人也可以有别的活法,不用困在小院里看人脸色。不过,她不会唱戏,也不懂做买卖,想逃,连路往哪走都不知道。 张财主的咳嗽一声比一声重,书房里常年药味不散。月红端药经过,听见他和管家说:“我死后她若不守祠堂,就不客气。”那一刻她看明白,这所谓规矩,从她进门那天就当成了锁她一生的绳子。 夜里,她总被噩梦惊醒,梦里自己穿白衣坐在祠堂里,头发一点点白,最后像块冷石头。一觉醒来,枕边全是冷汗。她摸着枕芯里新塞进去的碎银子,心里一点点有了底气。 她把首饰拆成银片,借着上香的名头把香火钱也一点点揣进袖子,托翠儿探路,哪条出城道盘查松,哪家店敢收留单身女工,散碎消息被她一点点织成一张逃生的网。 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后厨的王妈无意间说漏了嘴:祠堂那只老柜子里,“放着比银子还硬的东西”。那夜,张财主喝了安神汤昏睡,她摸出刻着鲤鱼纹的铜钥匙,悄悄打开柜门。 眼前没有金银珠宝,只有厚厚一柜欠契黑账,还有一张泛黄的祖训。纸上写得清清楚楚:“张家男子守德,媳妇才需守节。”传到如今,前半句被人当没看见,只拿“守”字压女人。 她这才明白,张家人用来栓她的祠堂和规矩,本身就是歪着用的东西。既然如此,与其一逃了之,背着“不守妇道”的骂名东躲西藏,不如先用这堆账册,把压在自己头上的枷锁撕开一道口子。 张财主断气那天,满屋族老围着灵柩念规矩,月红却把桌上一摞账本“啪”地拍在案上:“守祠堂可以,不过得写清楚。佃户三年免租,欠契重算,妇人规矩也要抄在纸上,别只逼媳妇守节。” 族长脸一黑,正要发作,她翻开几页黑账,谁侵公田、谁虚报田亩,一条条摆在眼前,屋里一下安静。族长背上渗出冷汗,只能咬牙点头,这场谈判,她拿着别人的把柄,为自己换出一点公道。 进祠堂那夜,她没有翻墙,而是在门口撒下一层米粉。果然有人半夜摸进来想偷账本。第二天,她指着清晰的脚印质问:“谁敢半夜进祖宗屋子翻东西。”人群里有人脸色煞白,从此再没人敢夜闯祠堂。 白天,她在祠堂支起桌子,教穷孩子认字写字,把欠契一张张誊出来,让佃户按手印抵账:“按了印就算还清。”阴森森的祠堂里竟多了股学堂气。有人骂她亵渎先人,她只淡淡一句:“祖宗看见后人有饭吃、有书读,只会高兴。” 一年期满,族长依约送她出祠堂。有人等着看笑话,以为这回她非得赖在张家。她却在镇口租下小铺,卖记账纸和学堂纸,把祠堂里的那点学问真正搬到了街面上。 车老板提着聘礼上门,她笑着摇头:“再等等,我想先把学堂办稳。”有人问她当初怎么不逃,她说:“逃,是把旧账一刀斩断;改,是在原来的秩序里重写规矩。被人逼着守叫枷锁,自己定下的守叫路标。” 在祠堂砖缝里顽强钻出来的野草,不是被风吹着摇的那根“守节牌坊”,而是会往有光处一路伸的命。月红握住那把铜钥匙时,握住的不只是账册和黑账,更是自己这条路的方向。 后来镇上有人悄悄讲她的故事,说她不是不守规矩,而是把规矩扭回了原本的样子。那些当年想拿祠堂锁住她的人,再也不敢提“守三年”来吓唬别的姑娘了。她用一年的祠堂,把一辈子的祠堂拆成了路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