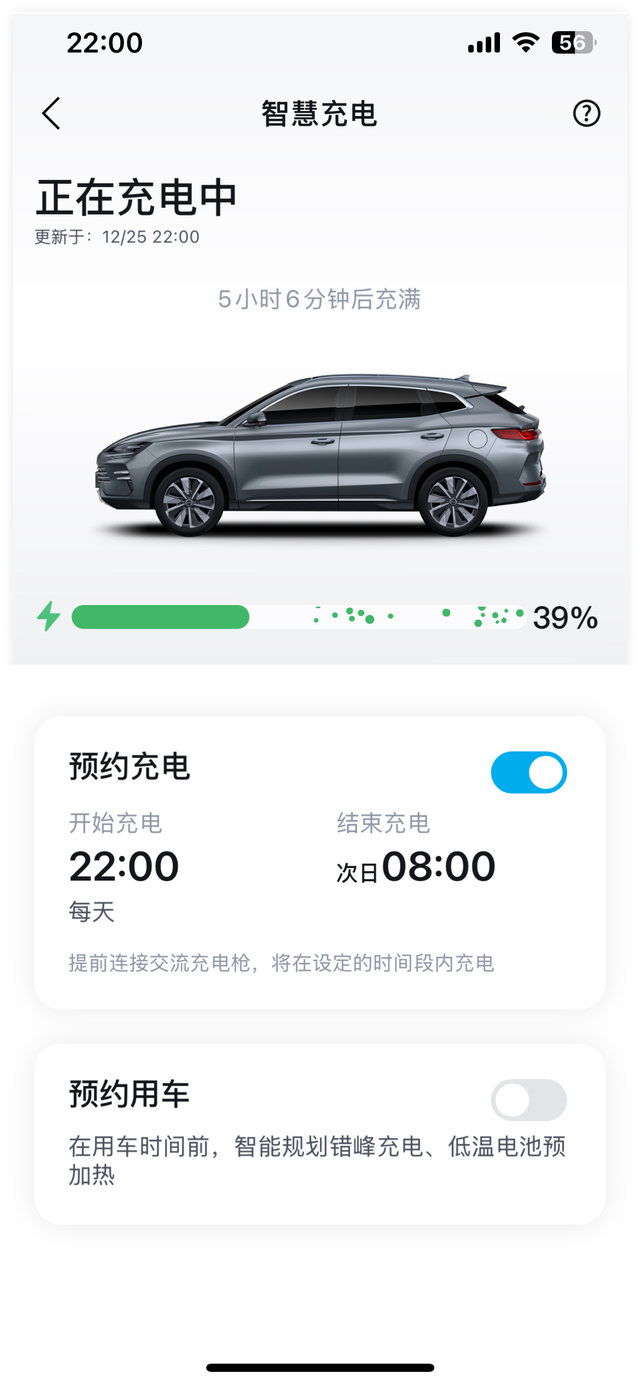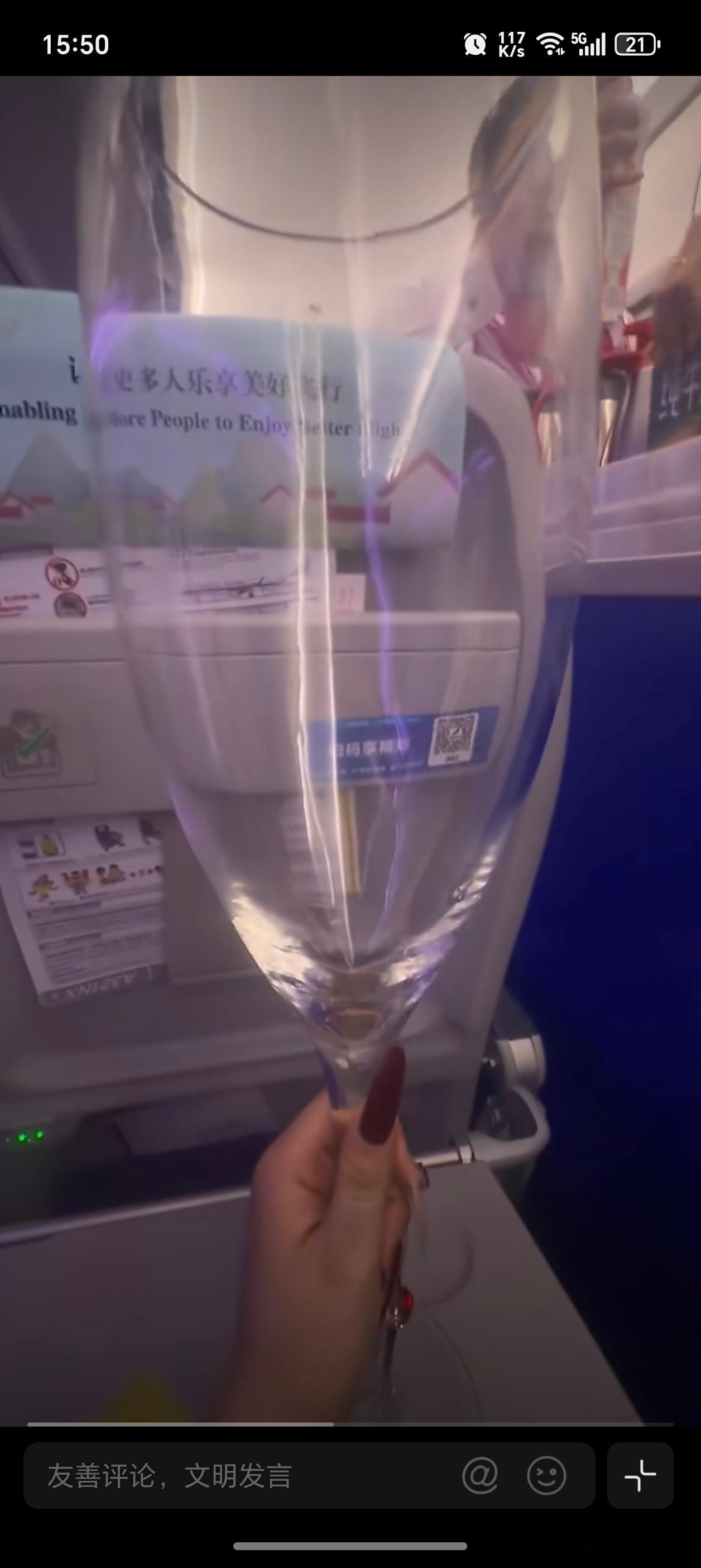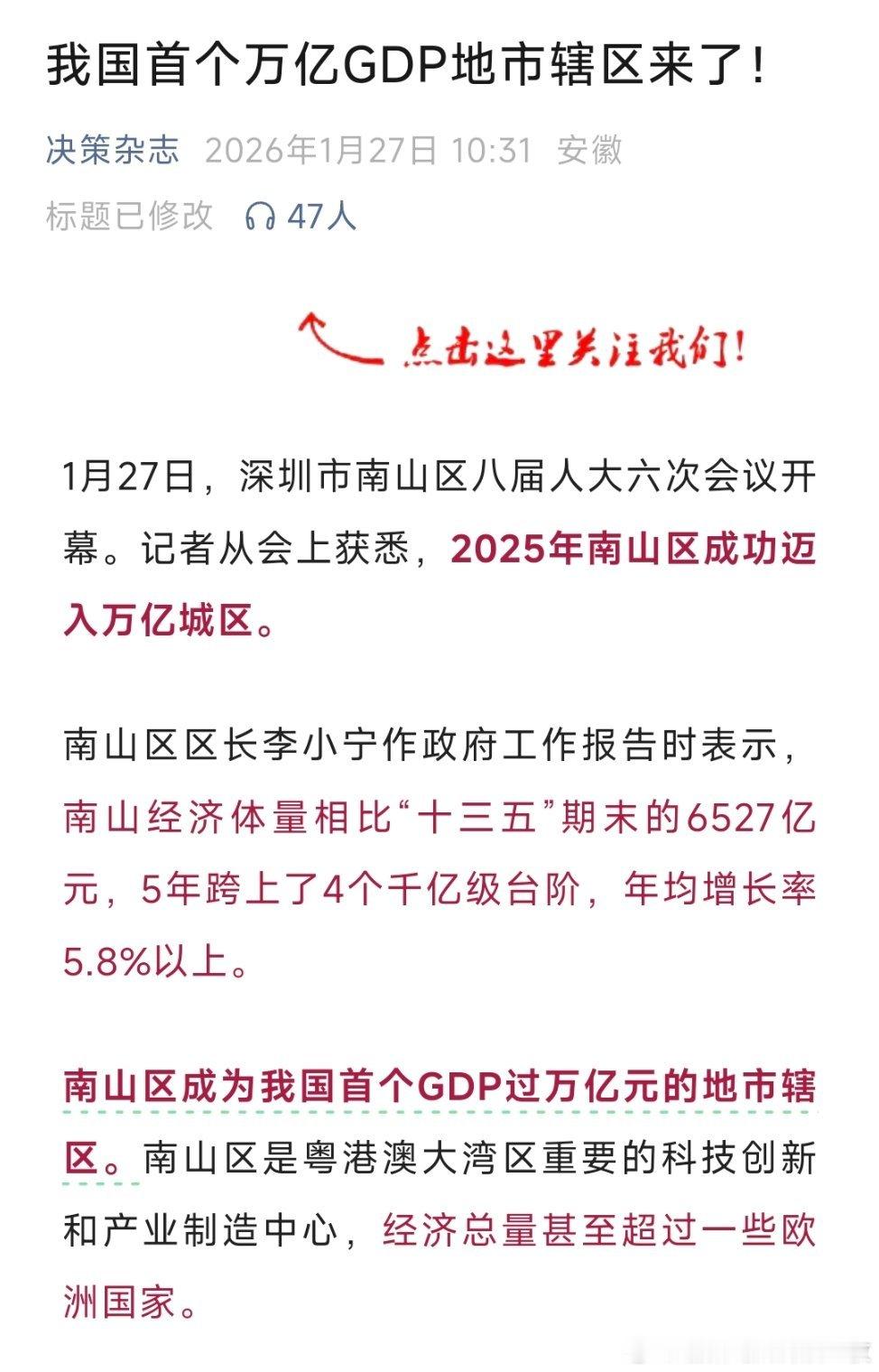1979年,上海知青戴建国不顾反对娶了一农村女子,谁知娶回家当晚,妻子就大喊大叫,冲过去一拳将他打得流鼻血,撕了他书稿,事后,岳母叹气道:“你丢下她,自己回上海生活吧!”哪料他却眯着眼笑道:“没事,我喜欢!” 这婚结得,整个村都当笑话看。洞房花烛夜,新娘子桂香不是羞答答坐着,倒是像受了惊的驴子,瞪着眼喘粗气。戴建国刚想把誊了半年的复习手稿收进木箱,她就扑上来了,拳头没轻重地撞在他鼻梁上,血顿时糊了一嘴。纸页嘶啦作响,碎得像雪片,那可是他熬了无数夜、指望靠着回城考学的命根子。外头听热闹的乡亲扒着窗户缝,窃窃私语传得比风还快:戴知青这回可算栽进火坑了,讨了个疯婆娘。 岳母第二天一大早就蹲在门槛边上抹眼泪,话里透着认命的苦涩:“建国,咱家对不住你。桂香这病……打小就这样,见着书本纸笔就犯癔症,谁也没敢说。你走吧,回你的上海去,这婚姻就当没发生过。”老太太心想,这上海来的俊后生,细皮嫩肉还会写字,怎么可能甘心被个疯女人拴在这黄土沟里? 戴建国却真没走。他拿凉水拍净了鼻血,蹲在地上把碎纸片一页一页捡起来,眯缝着眼,嘴角还挂着那点笑:“没事,我喜欢。”这话说得轻,却把岳母震住了。村里人只当他是书读多了迂腐,或是城里人脸皮薄不好意思立刻反悔。没人知道,昨晚桂香发狂前,他瞥见了她那双眼睛,不是疯癫,是怕,怕得浑身发抖,像被逼到墙角的小兽。她砸他撕纸的时候,嘴里含糊嚎的是“别抓我!烧了!全烧了!”那模样,让他心口像被碾过一样,闷闷地疼。 他留下来了。白天跟着队里下地,活儿干得生疏却肯卖力气;晚上就着煤油灯,把碎纸片一点点拼凑,拿米饭粒黏。桂香缩在炕角盯着他,警惕又困惑。他不急,也不靠近,有时哼几句上海的小调,有时对着黏好的书页自言自语:“这段公式可不好记……唉,这页缺个角,得猜猜了。”过了七八天,他故意把黏好的几页稿纸“忘”在灶台上。第二天发现,纸好好地在那儿,边上却摆着两个洗干净的红薯。 他慢慢摸出点门道。桂香不是恨书,她是怕。怕到什么程度?一见印着字的纸就脸色发白,浑身紧绷。戴建国想起以前听老人闲聊,说早些年这村子闹得厉害,有个教书先生被拖去批斗,怀里揣的诗集当场被烧,先生没多久也投了河。他没敢直接问,只旁敲侧击地向村里老人打听。果然,桂香的爹,就是那个教书先生。她那时才六七岁,眼睁睁看着爹的書被点燃,人像片叶子般飘进河里。从此,书本、纸张、墨水的味道,于她不是知识,是家破人亡的恐惧,是烙进骨头里的惨痛印记。 他换了个法子。不再拼书稿,转而用树枝在泥地上画。画小河,画飞鸟,画上海外滩的钟楼。桂香起初躲得远远的,后来蹲在几步外看。有一天,他画了辆拖拉机,画得歪歪扭扭。桂香忽然小声说:“轱辘……画扁了。”戴建国心头一跳,捡了块石子递过去:“那你改改?”桂香犹豫好久,蹭过来,飞快地在地上划了几道,拖拉机轱辘果然圆了。那是她第一次,没有因为“画”和“字”而尖叫。 日子像村边的小溪,静静淌着。戴建国报名高考的信寄到公社那天,他拿着信封回家,桂香又明显僵了一下。但他当着她的面,慢慢拆开,抽出信纸,然后轻轻拉过她的手,把信纸放在她手心。“这是纸,”他说,“也是路。但不是烧人的火,是照路的灯。我想带你一起走的路。”桂香盯着那张纸,手指颤抖,却没撕。眼泪大颗大颗砸在纸上,洇湿了公章的红印。 后来,戴建国考回了上海。离开村子那天,桂香紧紧挨着他,怀里抱着个蓝布包袱,里面整整齐齐包着的,是他全部黏好的书稿。岳母送他们到村口,哭得说不出话,只是用力拍戴建国的手臂。 很多年后,戴建国成了大学教授,桂香在学校的印刷厂找到份工作,见了油墨纸张也不再害怕。有人问戴教授,当年怎么看上这么个“乡下疯丫头”。他依旧眯着眼笑,说:“她那不是疯,是伤。我喜欢的,是那个能把我画歪的轱辘改圆了的姑娘,心里有谱,手上有准头。” 感情这事儿,有时候就像戴建国黏那些碎纸片。旁人看着是一堆破烂,毫无价值,黏它作甚?可偏偏有人,能在碎片里看见原来的花纹,肯花耐心,一点点拼凑,用最笨的功夫,等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完整。他看见的,不是“疯”,而是恐惧背后那个受伤的小女孩,以及破碎之下尚未湮灭的灵巧与真实。那个年代,多少结合始于无奈,困于现实,可他偏从无奈里生出了理解,从困局里长出了温柔。这或许不是传奇,只是一个普通人,在不普通的境遇里,选择了不普通的看见与坚持。看见伤痕之下的那个人,坚持用日子当米粒,去黏合两颗同样破碎过的心。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