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位老妇人请汉奸侄子吃饭,突然压低声音问道:“侄儿,能不能给我弄300发子弹。” 谁知,汉奸侄子听后瞬间变了脸色:“你要子弹干什么?”“给游击队。”只听见桌子啪的一声,侄子噌的一下站了起来,厉声说道:“你不想活了?” 这个老妇人叫马宗英,看着就是个普通农妇,在山东日照莒县卖包子、烧饼过日子。可没人想到,她其实是游击队的地下联络员,专门在日伪眼皮底下传递情报、运送物资。 那时候日本兵在山东横行霸道,杀人放火、欺压百姓,马宗英亲眼见过乡亲被活埋,村庄被炸成废墟。这些事深深刺痛了她的心,她就想尽自己的一份力,帮八路军打鬼子。 侄子这一拍,把隔壁桌的酒鬼都吓得一哆嗦。马宗英却眼皮都没抬,慢悠悠夹起一块猪头肉,蘸了蒜泥放进嘴里,嚼得咯吱响。她抬眼盯着侄子,那眼神像在说:你小子穿这身狗皮,就真把自己当狼了? 侄子叫马德贵,小时候发烧,是马宗英背着他跑了十里地找郎中。如今他当了伪军小队长,袖口三道金线,走路都带风。可他知道,这风是鬼子吹的,一吹就散。他瞅着姑姑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忽然想起那年冬天,姑姑把唯一的棉被剪了,给他缝了条棉裤。 “坐下。”马宗英声音不大,却像秤砣砸在心上。马德贵僵了半秒,屁股挨回板凳,像挨了枪子。 “你以为我傻?”马宗英用筷子头戳他胸口,“你当汉奸那天,我就知道你早晚得还。”她掏出个粗布包,啪地拍在桌上,布角散开,露出半截银镯子——那是马德贵他娘留下的遗物。“你娘托梦给我,说你在阎王簿上勾了名,得用三百发子弹赎。” 马德贵喉咙发紧。他想起上个月,鬼子让他带路去“清乡”,他眼睁睁看着翻译官把三岁娃娃扔进井里。那晚他喝了三斤地瓜烧,吐得胆汁都出来了,可第二天还是得陪着笑,把抢来的母鸡拎去鬼子队部。 “子弹藏在粮车底下,明晚三更,西沟门。”他声音哑得像砂纸磨锅,“姑姑,你欠我条命。” 马宗英笑了,脸上的褶子像干裂的馒头掰开,里头却是白的。“命是欠,可欠的是中国人,不是你。”她起身,把银镯子推回去,“留着吧,等你哪天想当人,再戴。” 第二天夜里,粮车吱呀呀出城。马德贵骑着洋车子在前头,后头跟着俩伪军。他哼着小调,心里却敲鼓。西沟门黑得像锅底,突然一声布谷鸟叫,粮车“咔嚓”陷进坑里。伪军骂娘,弯腰推车,黑影里窜出几条人影,三下五除二把枪卸了。马德贵腿一软,跪在地上,却听见熟悉的声音:“小子,挺准时的。” 游击队接过子弹,拍拍他肩膀:“算你还有点人味。”马德贵想笑,嘴角却抽成苦瓜。他回头,看见姑姑站在沟沿,背影像棵老槐树,风一吹,叶子哗啦啦响,像在喊:回家。 可家在哪?鬼子据点里,他的办公桌摆着天皇像;回村?汉奸的牌子能砸死人。马德贵蹲在地头,摸出银镯子,对着月亮瞅。镯子内侧刻着个小字:诚。他忽然嚎啕大哭,像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 后来,马宗英的联络点暴露。鬼子把全村人赶到打谷场,机枪架好,翻译官喊:“交出马老太,不然都得死!”人群里,马德贵穿着伪军服,手死死攥着枪套。马宗英被绑出来时,冲他笑了笑,那笑像刀子,把他胸口划开。 枪响了,不是机枪,是马德贵。他打死了翻译官,把枪扔向游击队方向,转身扑向鬼子队长,抱住了同归于尽的手榴弹。爆炸声里,银镯子飞上天,落在马宗英脚边,没沾血,亮得刺眼。 战后,莒县立了块无名碑。马宗英每年清明都去,拎一篮包子,放仨在碑前。“德贵啊,”她对着风说话,“子弹我收到了,镯子也给你留着,下辈子,别再当狗。” 写这故事时,我老想起一句话:汉奸也是人,可有时候,人得先撕了自己,才能做人。马宗英没念过书,但她懂——枪口抬高一寸,是活路;抬高一尺,就是脊梁。她拿三百发子弹,赌侄子心里那点人味没死透。她赢了,也没赢,因为命换命,账永远算不清。 今儿个我们说起抗日,爱拍手撕鬼子,可我更想记住马宗英这样的老太:包子铺的蒸汽熏得她眼泪直流,她却把眼泪攒成河,淹鬼子的脚。她没喊口号,只说一句:“咱不能让人白死。”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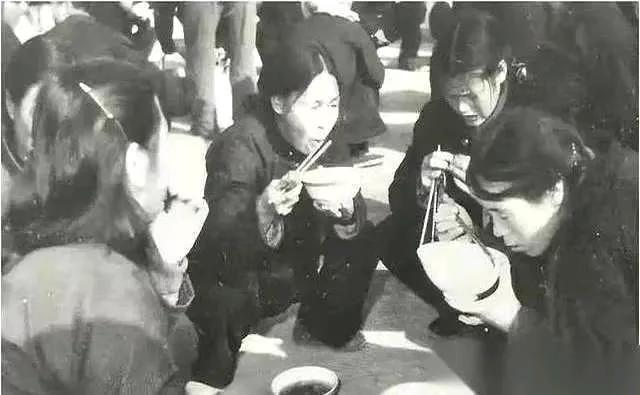

![张雪峰炸出一堆汉奸出来[笑着哭]](http://image.uczzd.cn/5285732039243402149.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