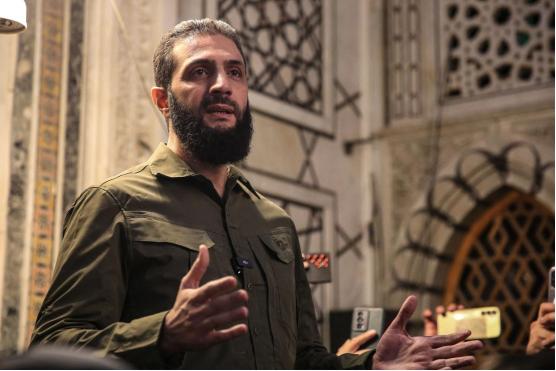最近基辛格早年的预言又被翻了出来,老爷子当年就说,俄乌打下去,最先耗干的不是俄罗斯,不是美国,更不是那些跟着起哄的小国,而是一个谁都没太往深处想的国家,基辛格一辈子搞外交,经历过冷战、二战,对大国博弈门清, 从经济数据看,欧盟作为俄罗斯能源的传统买家,在冲突爆发后不得不迅速调整能源政策,2022年,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占总进口量的比例从战前的约40%骤降至不足10%。 这种急剧转变带来的价格飙升和供应不稳定,使欧洲各国付出了沉重经济代价,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能源价格冲击使欧盟在2022-2023年间损失了约1.5%的GDP增长。 军事援助方面,欧洲各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装备,许多国家自身的武器库存降至危险水平。 德国联邦国防军的一份内部报告显示,德军现有装备仅能满足北约最低要求的一半,这种军事资源的持续外流,正在削弱欧洲的长远防御能力。 政治层面上,俄乌冲突加剧了欧盟内部分歧,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与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在制裁俄罗斯、援助乌克兰问题上立场迥异,这种裂痕正在挑战欧盟的团结和决策效率。 更深远的影响是,俄乌冲突正在重塑欧洲的安全认知,一直依赖美国安全保障的欧洲国家,突然意识到自身处于地缘政治对抗的前线。 波兰迅速将国防预算提升至GDP的4%,德国设立了1000亿欧元的特别国防基金,这些变化反映了欧洲安全范式的转变。 基辛格的预言建立在他对历史格局的深刻理解上,在他看来,欧洲一直处于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缓冲与博弈地带,而欧洲国家常常低估了自身在这种博弈中的脆弱性。 他在2014年就曾警告,乌克兰危机可能成为“欧洲分裂的开始”,而非东西方矛盾的终结。 与许多关注俄罗斯耐受力或美国承诺可靠性的分析不同,基辛格将目光投向了欧洲,因为他明白,地理上接近冲突、经济上与俄罗斯交织、政治需要团结27个成员国、军事上长期依赖美国的欧洲,才是这场持久冲突中最易受伤的发达经济体。 欧洲面临的困境是多重的,既要替代传统能源供应,又要维持绿色转型步伐,既要满足国内社会福利需求,又要增加国防开支,既要支持乌克兰,又要避免冲突无限升级,这种多线作战正在消耗欧洲的战略资源和凝聚力。 历史经验表明,大国竞争中最先显疲态的往往不是直接对抗的双方,而是那些被卷入漩涡却又无法主导局面的重要力量,就像冷战时期,美苏最终寻求缓和,而许多参与其中的盟友却已饱经沧桑。 基辛格的预言之所以引人深思,在于它揭示了国际政治中一个常被忽视的真相,在地缘政治博弈中,最脆弱的往往不是直面冲突的国家,也不是远离冲突的强国,而是那些身处冲突边缘却又深度卷入的次强国。 欧洲今天的困境源于多重身份的矛盾,作为价值观共同体,它需要支持乌克兰,作为经济联盟,它需要稳定与繁荣,作为安全实体,它依赖美国保护。 作为全球行为体,它寻求战略自主,这些相互冲突的身份在和平时期尚可平衡,在危机中却成为无法调和的矛盾。 欧洲的消耗不仅体现在经济数字上,更表现在战略自主性的丧失,俄乌冲突本应是欧洲推动自身防务建设的契机,然而现实是,欧洲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反而加深。当德国需要美国的核保护伞,东欧国家渴望美军永久驻扎,法国倡导的“战略自主”显得苍白无力。 更深层次看,欧洲的困境是全球化退潮的缩影,过去三十年,欧洲享受着和平红利与全球化红利,将经济效率置于安全考量之上,建立了包括俄罗斯能源在内的跨国供应链。 俄乌冲突标志着效率让位于安全的时代来临,而转型成本大部分由欧洲承担。 基辛格的智慧在于他理解国际政治的“第二序效应”,决策的直接后果往往不如间接后果重要。 俄乌冲突的第一序效应是乌克兰的抵抗和俄罗斯的受挫,而第二序效应可能是欧洲的持续削弱和全球重心的进一步转移。 对世界而言,欧洲的消耗意味着多极化进程中一支稳定力量的减弱,相比新兴大国,欧洲更倾向于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它的削弱可能导致全球治理进一步碎片化。 基辛格的预言提醒我们,在国际关系中,最危险的处境往往不是明确的敌对,而是模糊的中间地位,既非交战方也非旁观者,既要付出代价又无法掌控局势。 欧洲今天的困境,或许也是其他在地缘政治夹缝中求生存国家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