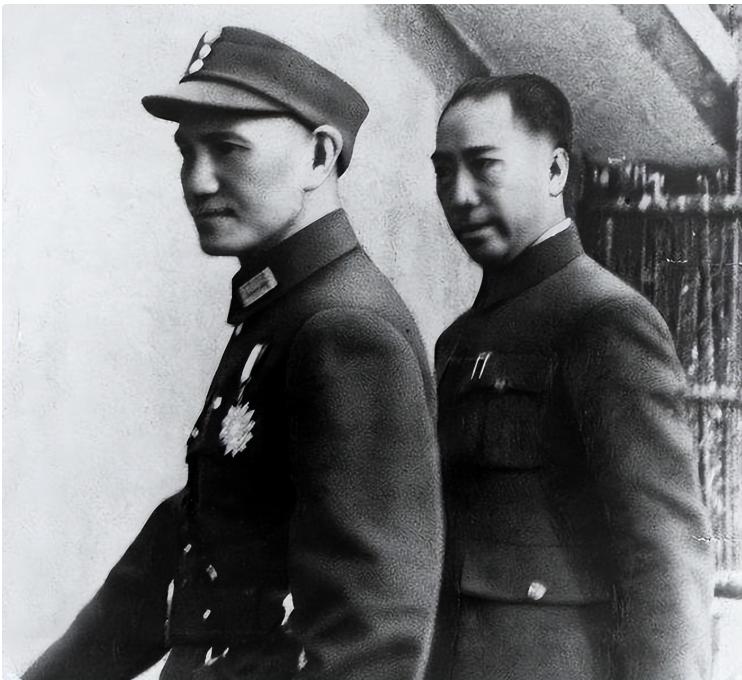1991年,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善来到北京,打算收回父亲购置的四合院,但住户拒不承认,并要求每户赔偿几百万,无奈之下,杜维善只能求助相关部门,那杜维善最后有没有收回房产呢? 1991年冬天,年近六旬的杜维善穿着地质考察装站在北京东城区那个大杂院门口时,没人觉得他有什么不一样,他怀里揣着民国时期的泛黄地契和纳税单,这可是他在温哥华翻箱底找出来的宝贝,也是他此时唯一的筹码。 但这筹码在现实面前有点轻飘飘,院子是好院子,东四轿子胡同8号,四百多平米,当年杜月笙为了孟小冬唱戏练嗓专门置办的。 这宅子讲究,中西合璧,承载着梨园冬皇的余音,可到了1991年,这里早没了当年的清净,二十多户人家挤在里面,这就是个典型的大杂院。 杜维善早就没了富家公子的傲气,虽说他出生在1933年的上海,母亲又是京剧名伶姚玉兰,但“杜家七少爷”的光环就像个肥皂泡。 抗战躲在重庆时,天天吃面条的日子让他早早尝了穷滋味;等到1951年杜月笙在香港病逝,家里没了顶梁柱,十八岁的他就更得靠自己。 他也没指望吃祖宗饭,高中读完就跑到澳大利亚钻研地质学,那几年那是真苦,下矿井挖石头,去屠宰场杀猪宰牛,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 毕业后回到台湾做石油勘探,后来定居加拿大,那就是个标准的实干派技术员,这次回国讨房,也不是为了摆阔,实在是这房产算是家族最后的念想,不想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没了。 既然私下谈不拢,杜维善只能硬着头皮找官家,房产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办事倒是利索,翻出典藏的民国旧档,拿放大镜对着那些尘封的记录逐行比对,居然真就在那泛黄的册子里查实了当年的交易细节,银元数目对得上,杜月笙确实是业主。 但这理在法律上通了,情理上却还是堵得慌,评估师拿着尺子进场,这一量一算,结合当时政策,房子的折价和巨大的拆迁安置成本根本没法平衡。 整整一个冬天,杜维善在谈判桌和居民区之间来回跑,律师拟条款,代表们拍桌子,最后国家出面给兜了底:承认杜家的产权,但既然没法清退住户,那就由国家出钱买断这产权。 从十二月耗到次年三月,八十万人民币,这是最后敲定的数字,虽然跟市场估值或者住户要价差了十万八千里,但对于杜维善来说,这笔钱虽烫手,却也让这件事落了地,他在协议上签了字,看着那座依旧熙熙攘攘的大杂院,转身离去。 拿到了这八十万,杜维善转头干了件谁也没想到的事,他没买豪车,没置新业,反而一头扎进了古玩堆。 加上自己做生意的积蓄,他开始疯狂搜集丝绸之路上的古钱币,从萨珊王朝的银币到唐代西域的流通钱,凡是好东西,他就不惜重金往回买。 从1991年底开始,他先后七次把自己从海外淘换来的两千多枚珍稀古钱,一股脑全捐给了上海博物馆,他甚至连那一堆珍贵的外文研究典籍也一并送了出去。 信息来源:凤凰卫视——李菁:杜月笙之子欲要回北京老宅遇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