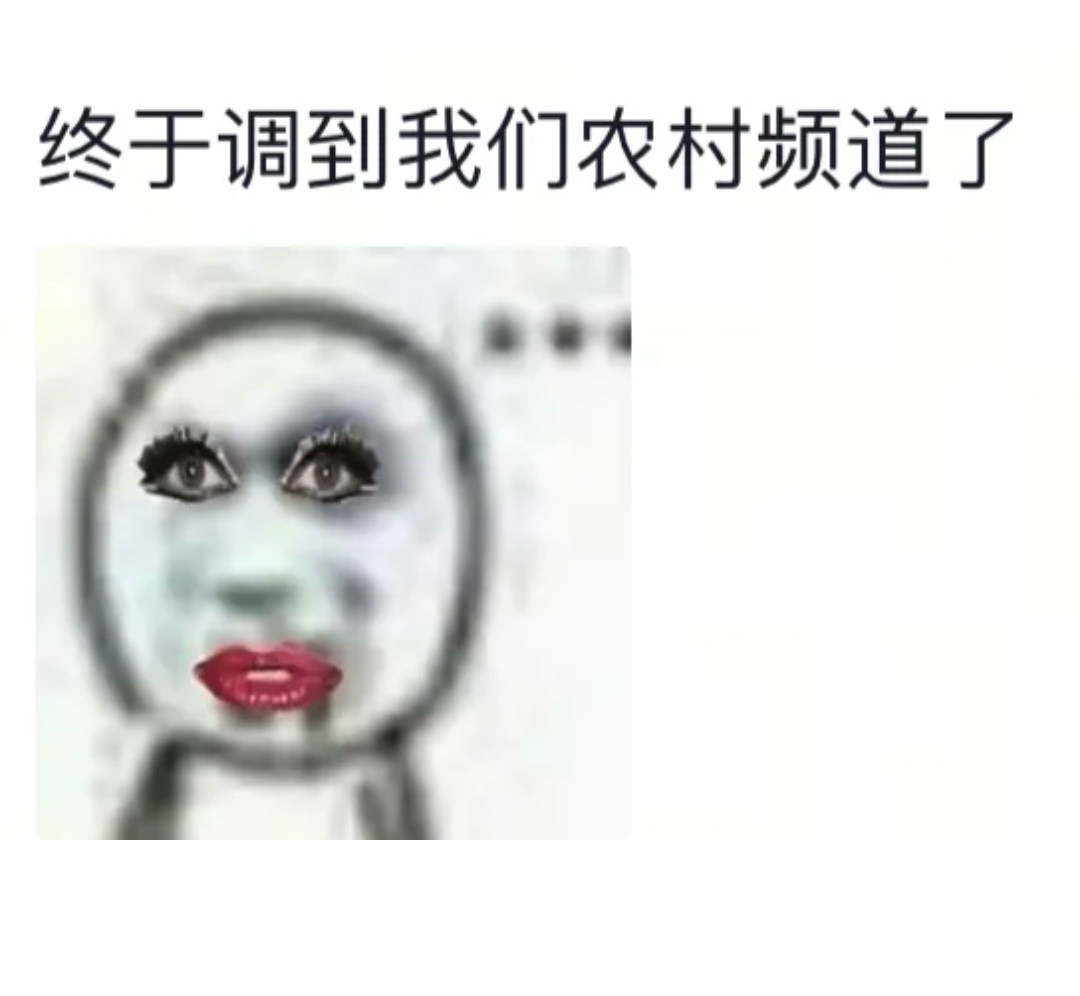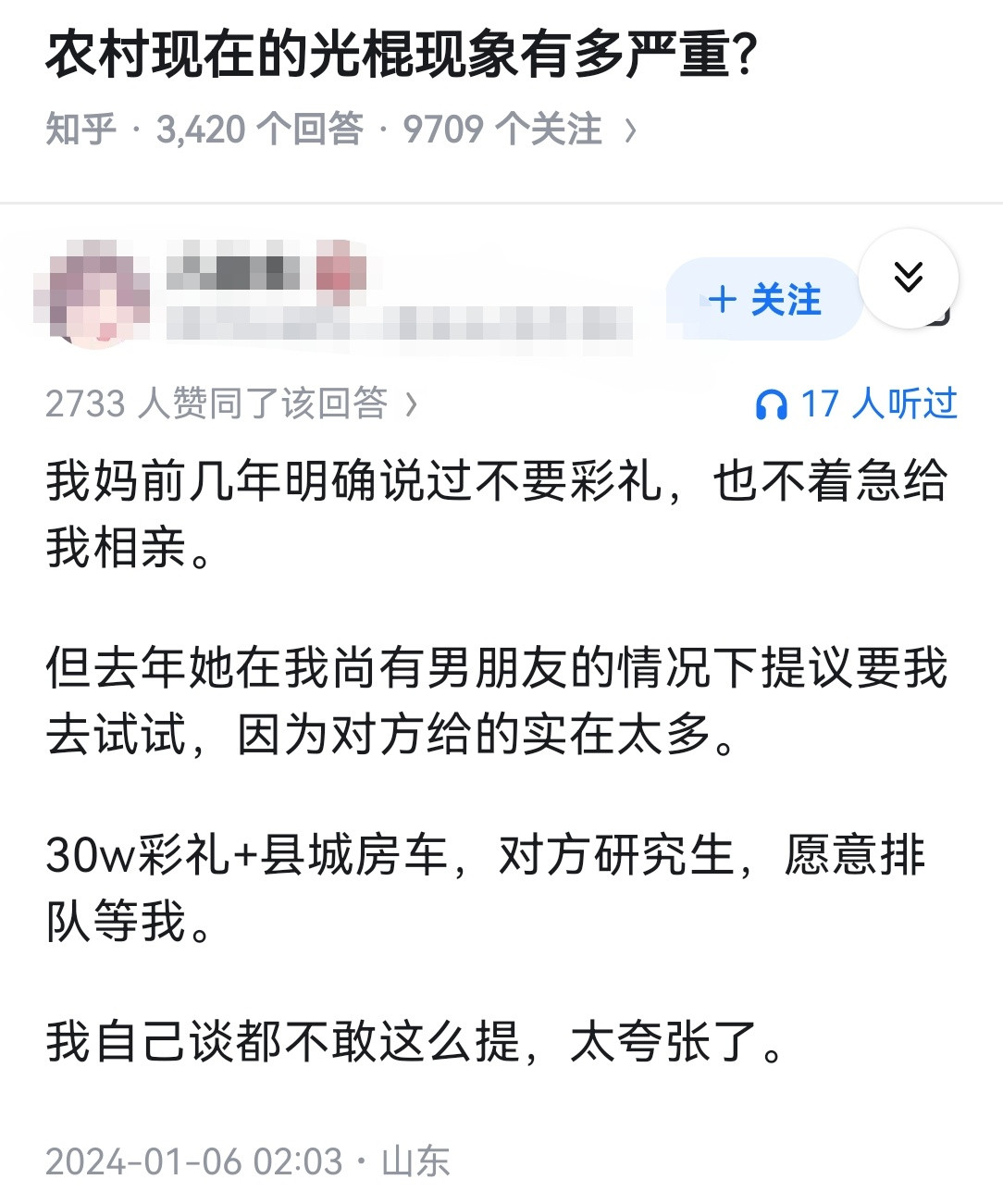我叫王根生,今年66岁了,从小就在农村长大。 老王的电话打过来,说今年的聚会定在重阳节,地点还是老地方,但人均费用提到了3000块。 手里的豆角突然变得滑溜溜的,怎么也捏不住。 这个数字让我心里发慌。 每月四千多的退休金,要留着给老伴买药,还要补贴刚创业的儿子。 本来想找借口说身体不舒服,但电话那头老王的声音带着不容拒绝的热情,说五十年的老兄弟了,少谁都不行。 挂了电话,手里的退休金存折被攥得发皱,这3000块,怕是要让这个月的日子紧巴巴。 记得1978年秋天背着干粮去军校报到的那天,北京站的风把我单薄的被子吹得哗哗响。 同宿舍的老王从北京城里带来的馒头,掰开分了我一半。 那时候我们挤在十二个人的宿舍里,晚上打着手电筒背战术理论,周末帮炊事班择菜换馒头票。 十二年的军营生涯,把我们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小伙子,熬成了能把后背交给对方的兄弟。 1994年第一次聚会时,我们二十几个人挤在三里屯的小烧烤店,AA制每人300块。 老王当时刚下岗,硬是找邻居借了钱也要来。 后来聚会的人均费用从500涨到1000,2015年提到2000的时候,有几个退休工资低的老伙计就开始缺席。 去年聚会只剩下十七个人,歌厅里唱《打靶归来》时,声音都没年轻时洪亮了。 今年春天儿子的装修公司资金周转不开,我把攒了三年的两万块养老钱都拿了出去。 本以为年底能缓过来,没想到老伴的降压药又涨了价。 接到聚会通知的那个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起身翻出那个褪色的军用挎包,里面装着1982年我们毕业时的合影,照片上的小伙子们穿着的确良军装,笑得露出白牙。 没想到一周后老王突然带着两个战友找上门来。 三个老头站在我家客厅里,老王从布袋子里掏出一个信封,说这是兄弟们凑的三万块,不光是今年的聚会费,还要帮我儿子周转生意。 我攥着那个沉甸甸的信封,手背上的青筋都鼓起来了,喉咙里像堵着团棉花,半天说不出话。 老王拍着我肩膀说,当年在战场上,哪个不是把生的机会留给兄弟,现在这点困难算什么。 更让我意外的是,这次聚会老王宣布了新规矩:以后聚会人均200块,剩下的钱成立战友互助基金。 原来这些年聚会剩下的钱,加上几个做生意的战友额外捐助,已经攒了三十多万。 基金专门用来帮助有困难的老伙计,还要资助战友们的子女上学。 那天在烧烤店,十七个老头举着茶杯碰在一起,茶水洒在桌上,像当年训练时流的汗。 现在我每个月都会去社区的退役军人服务站帮忙整理资料,把战友基金的故事讲给年轻的退伍兵听。 上个月有个刚退伍的小伙子创业遇挫,我们基金给他申请了一万元启动资金。 看着他敬礼离开的背影,突然想起1978年那个背着干粮袋的自己。 战友情这东西,从来不是酒桌上的热闹,而是五十年过去了,依然有人记得你爱吃的饺子馅,知道你哪段日子过得不容易。 前几天整理老照片,发现当年军校毕业照上的七十个人,现在能联系上的只剩二十三个。 老王说等明年春天,要带着基金的账本去给牺牲战友的家属看看,告诉他们,兄弟们没忘了当年的承诺。 窗外的玉兰花正开得热闹,我给照片上的老伙计们敬了个军礼,就像五十年前在训练场上那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