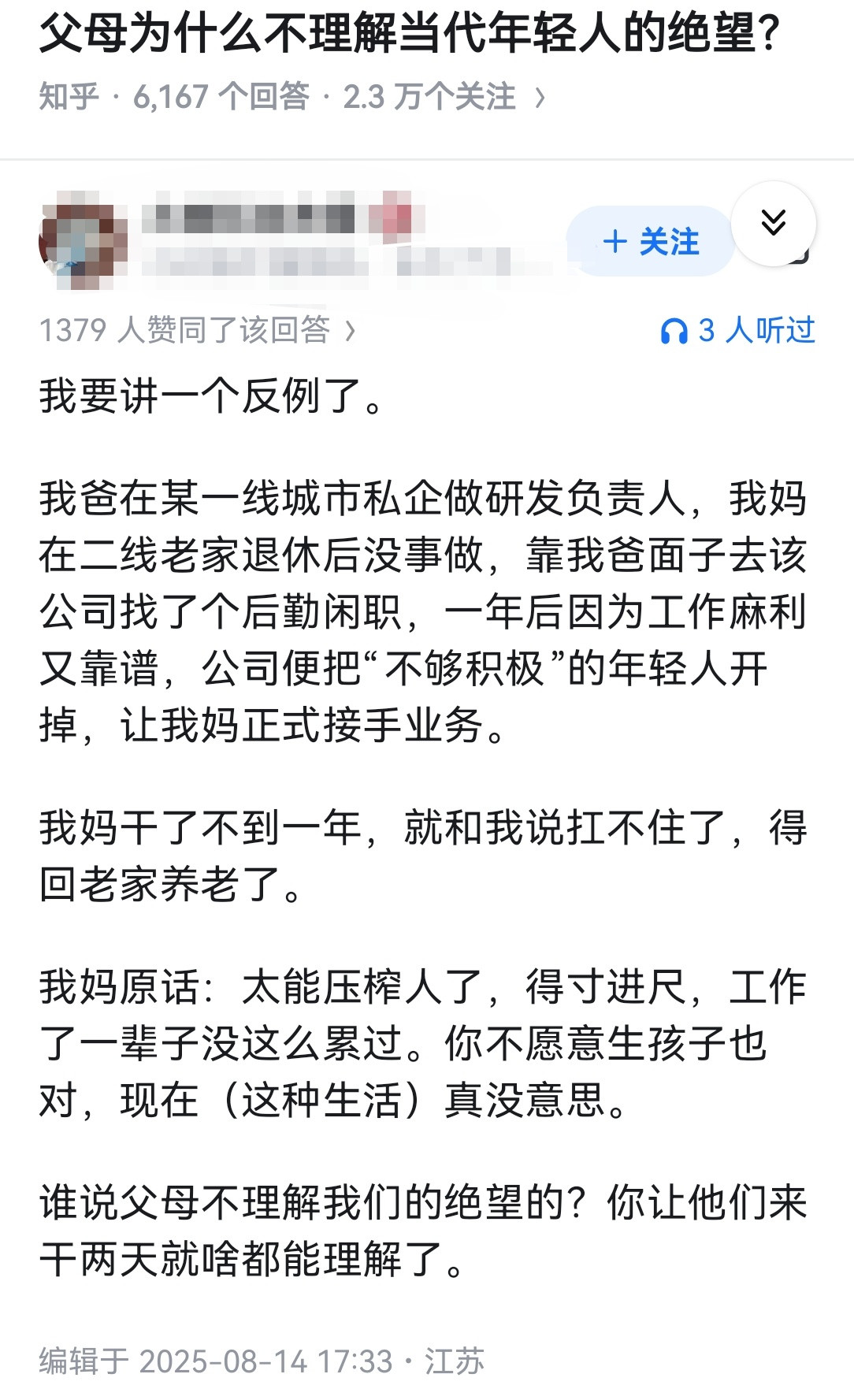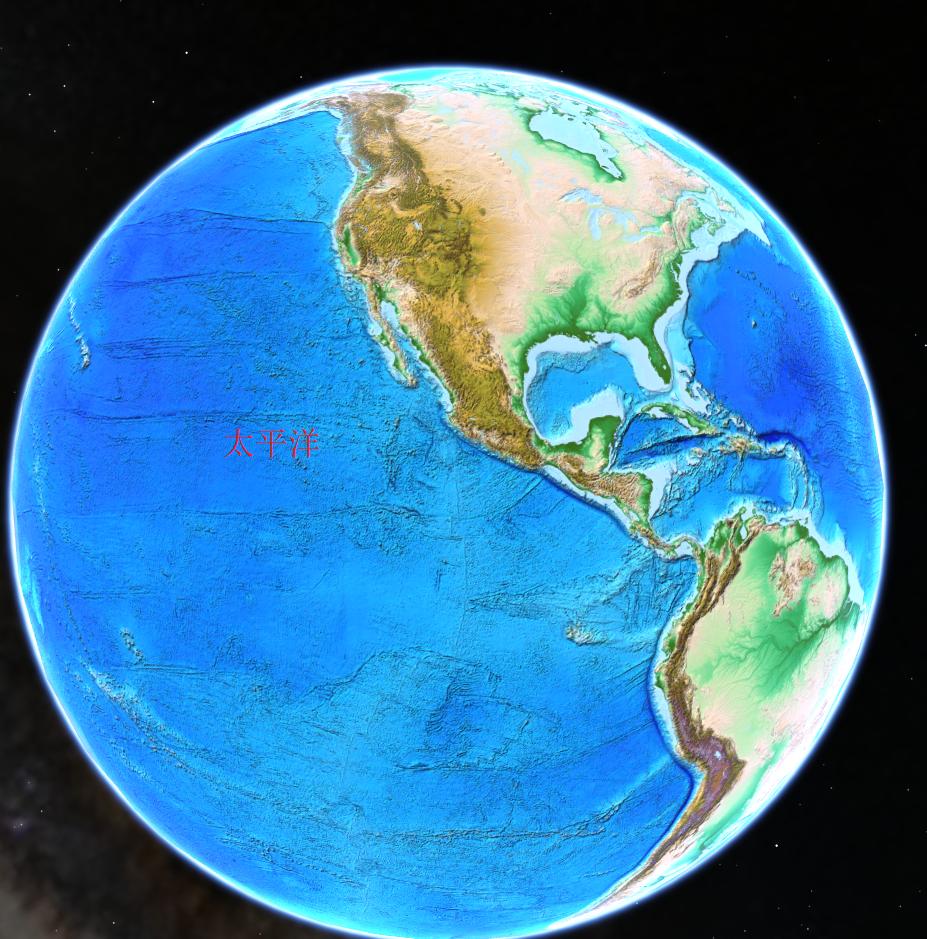建国前的三峡原来是这样的,充满了人间烟火味。这是1946年美国摄影师凯塞尔在三峡游历时拍摄的万县万安路,这个时候的万安路街头还有小时候记忆中的影子。 在凯塞尔的镜头下,1946年的万县美得让人心疼。大家看那张万州拱桥的照片,这座桥始建于清朝同治年间,横跨在竺溪河上。这桥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上面居然建了亭子。 这种“桥上盖房”的设计,是咱们老祖宗的智慧,既能保护桥身免受雨水侵蚀,又能给过往的商贩、百姓提供遮风挡雨的歇脚地。可惜,这座充满古典美感的桥,在1970年就被洪水冲垮了。 再看那张万安桥,建于1926年。照片里,万县的街道上已经竖起了电线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说明在1946年,这座古城已经通了电。 那种感觉很奇妙,古老的城墙、传统的长衫,旁边却是代表现代文明的电线杆,这种新旧交替的张力,正是那个时代的缩影。街头巷尾,有人在挑水,有人在摆摊,孩子们在石板路上疯跑。这时候的三峡,不是什么旅游景点,它是无数普通人实实在在的生活。 那时候的万县,依托长江水运,是川东最繁华的码头之一。但这种繁华背后,藏着巨大的隐患。 为什么?因为长江太险了。 凯塞尔的照片里,有一组最让人揪心的,是三峡纤夫。 现在的年轻人去三峡旅游,坐的是豪华游轮,看着“高峡出平湖”,觉得惬意得很。但在1946年,走长江简直就是闯鬼门关。 照片里,那些纤夫很多是一丝不挂,或者衣衫褴褛。这不是因为他们想耍流氓,是因为穷,也是因为衣服湿了干、干了湿,穿在身上反而会磨烂皮肤,导致溃烂感染。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皮肤感染是会死人的。 当时的陕江航道,险滩密布。最险峻的地方,一艘船逆流而上,每天最多只能前进200米。你没听错,一天几百米。几十里的水路,需要纤夫们喊着号子,把腰弯到几乎贴着地面,手脚并用地拉上十天半个月。 凯塞尔记录了一个令人咋舌的经济账:由于雇佣纤夫的成本太高,时间太长,如果船上装的货物不是特别贵重,很多船主算完账,干脆直接掉头回去,把货贱卖在当地,然后再走陆路进川。 这就是那个时代长江航运的真实写照:效率极低,成本极高,人命如草芥。 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万吨巨轮从重庆直达上海,运货量翻了5倍,航行速度快了不知多少倍时,一定要明白,三峡大坝的建设,不仅仅是为了发电,更是为了彻底终结这种“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水运历史。 除了人文,凯塞尔的镜头还记录了那些已经消失的地理奇观。 比如瞿塘峡的石板岬栈道。照片里,那条栈道像一条细线挂在绝壁上,那是古人一锤一凿硬生生在石头上抠出来的,全长9公里。看着照片,你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毅力和勇气。但现在,这条栈道已经永远沉入了江底。 还有白帝城。大家都背过“朝辞白帝彩云间”,在凯塞尔的照片里,白帝城是高高耸立在山顶的,扼守着长江咽喉,东望夔门,气势逼人。刘备当年就是在这里,含恨托孤。 而现在的白帝城呢?由于水位上涨,它已经变成了一座四面环水的“孤岛”,虽然依然存在,但那种“西控巴蜀,东扼荆楚”的险要气势,确实和古人看到的大不相同了。 最震撼的还是巫山。凯塞尔当时拍了一张俯瞰图。2003年蓄水后,巫山老城彻底没入水中。为了安置移民,国家在老城上方175米的高处,重新建了一座新城。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去的巫山县,其实是“巫山2.0”。真正的老巫山,那个有着千年历史、充满巴渝风情的老城,正安静地躺在我们脚下的深水中。 看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伤感。那么多古迹没了,那么多老家淹了,值得吗? 咱们得算大账。 2003年6月,三峡大坝首次蓄水,双线五级船闸通航。这一刻,彻底改变了长江的脾气。 以前长江跑大船,就像走独木桥,到处是激流险滩。现在是水面宽阔,波澜不惊。 更要命的是洪水。大家还记得98年大洪水吗?那种灾难,谁都不想再经历第二次。三峡大坝最大的功绩,其实是削减洪峰。专家算过一笔账,每挽回一次像98年那样的大洪水造成的损失,就等于白捡了一个三峡大坝的建设成本。 这是一举三得:防洪、航运、发电。利国利民,这四个字不是空话。 当然,为了这个宏伟工程,库区人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175米的蓄水高度,意味着654平方公里的土地沉入水底。像奉节老城,为了拆除,在2002年实施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爆破,用了1.6吨炸药。 但是,历史并没有被粗暴地切断。 对于那些珍贵的文物,国家也是拼了命地在保护。比如夔门摩崖上的十二幅古代书法真迹,是被一块块切割下来迁移的;大昌古镇那条1700年的青石板街,在8公里外的新址被一比一复刻;云阳张飞庙的搬迁精度,甚至达到了厘米级! 我们怀念老三峡,是因为那里有我们的根,有祖辈生活的痕迹,有那种原始而粗犷的美。 凯塞尔的镜头,锁住了1946年的时间;而我们的三峡大坝,锁住了长江的波涛。 这两者并不矛盾。历史藏在水底,未来立在潮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