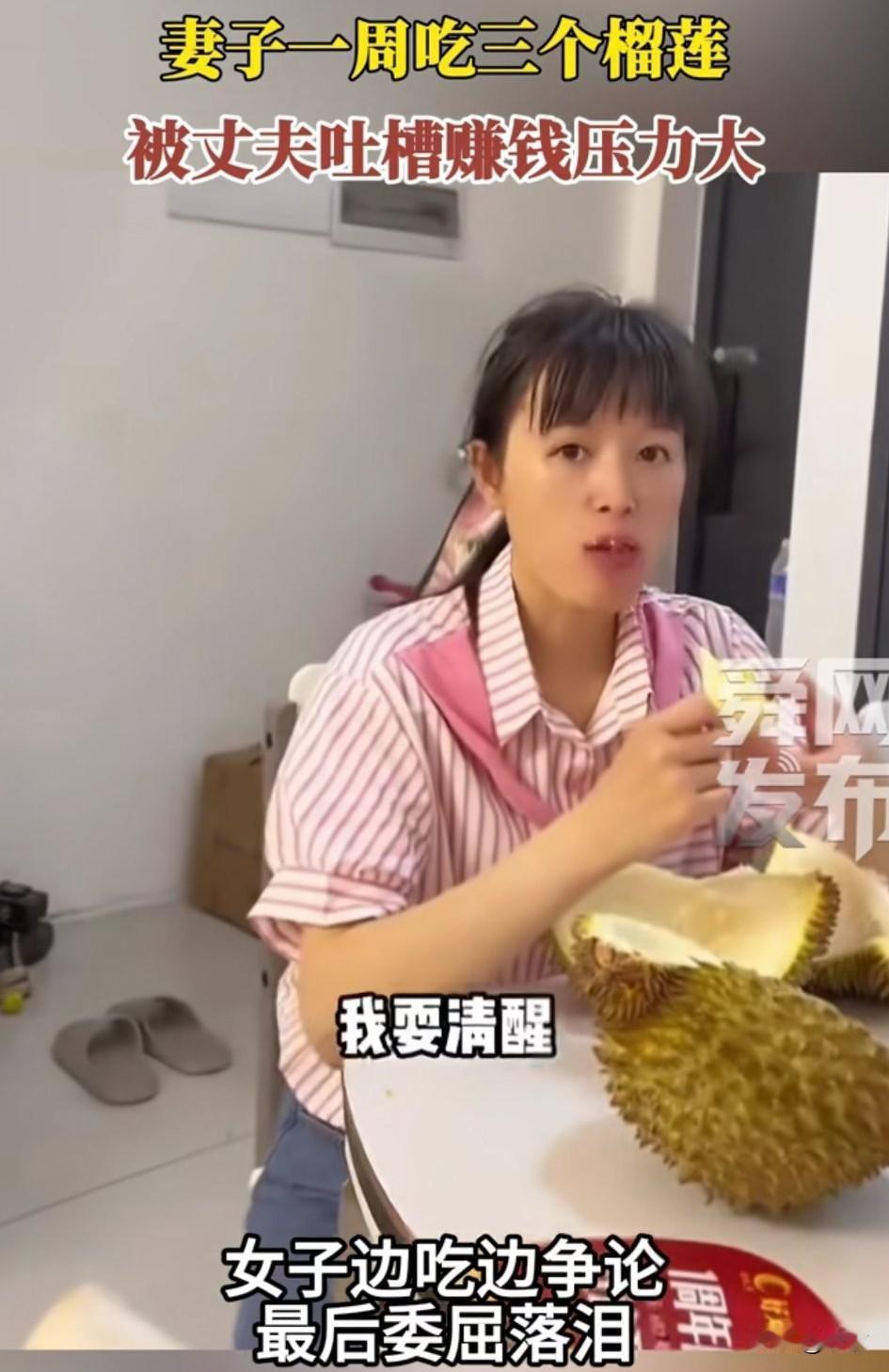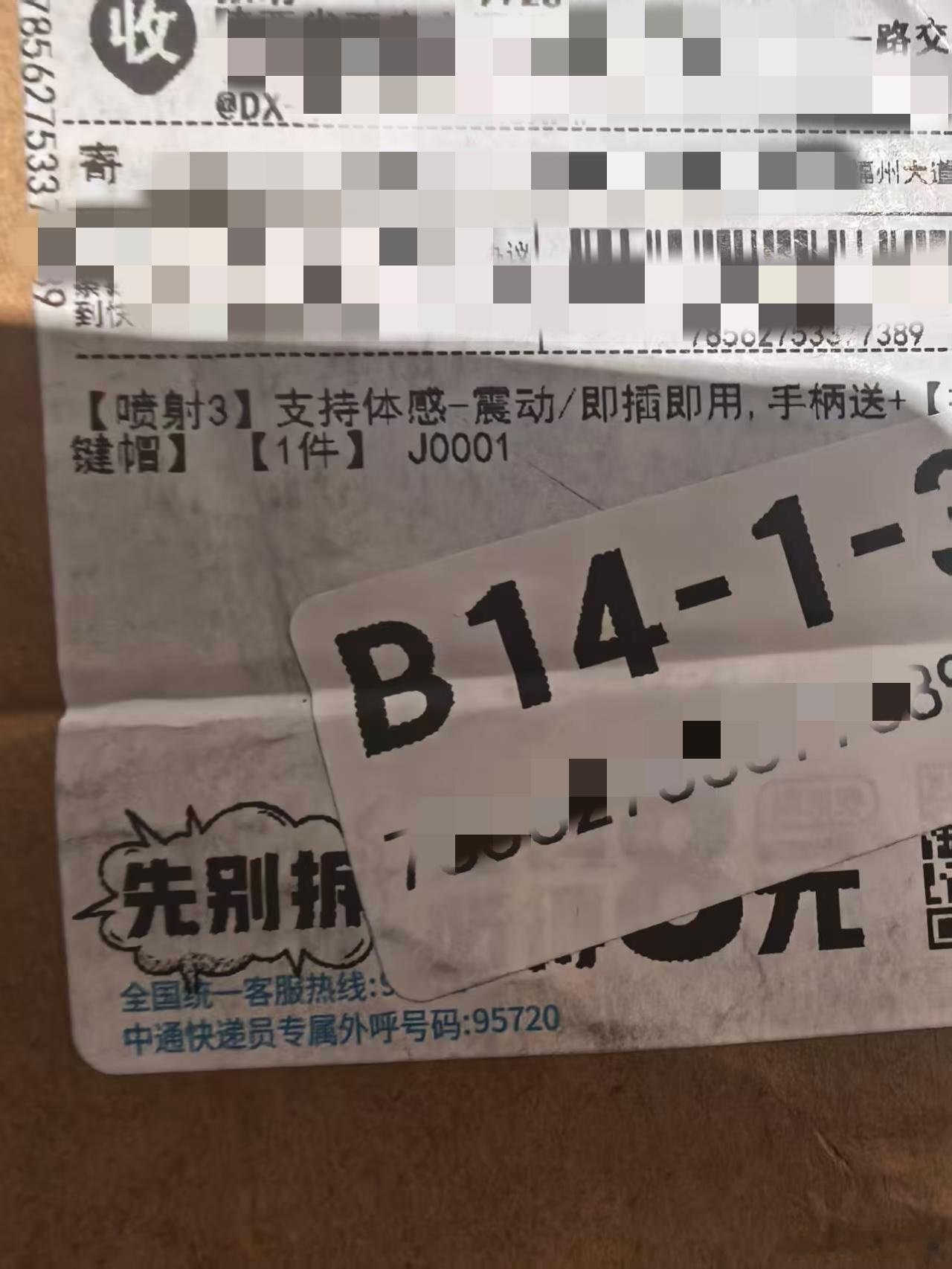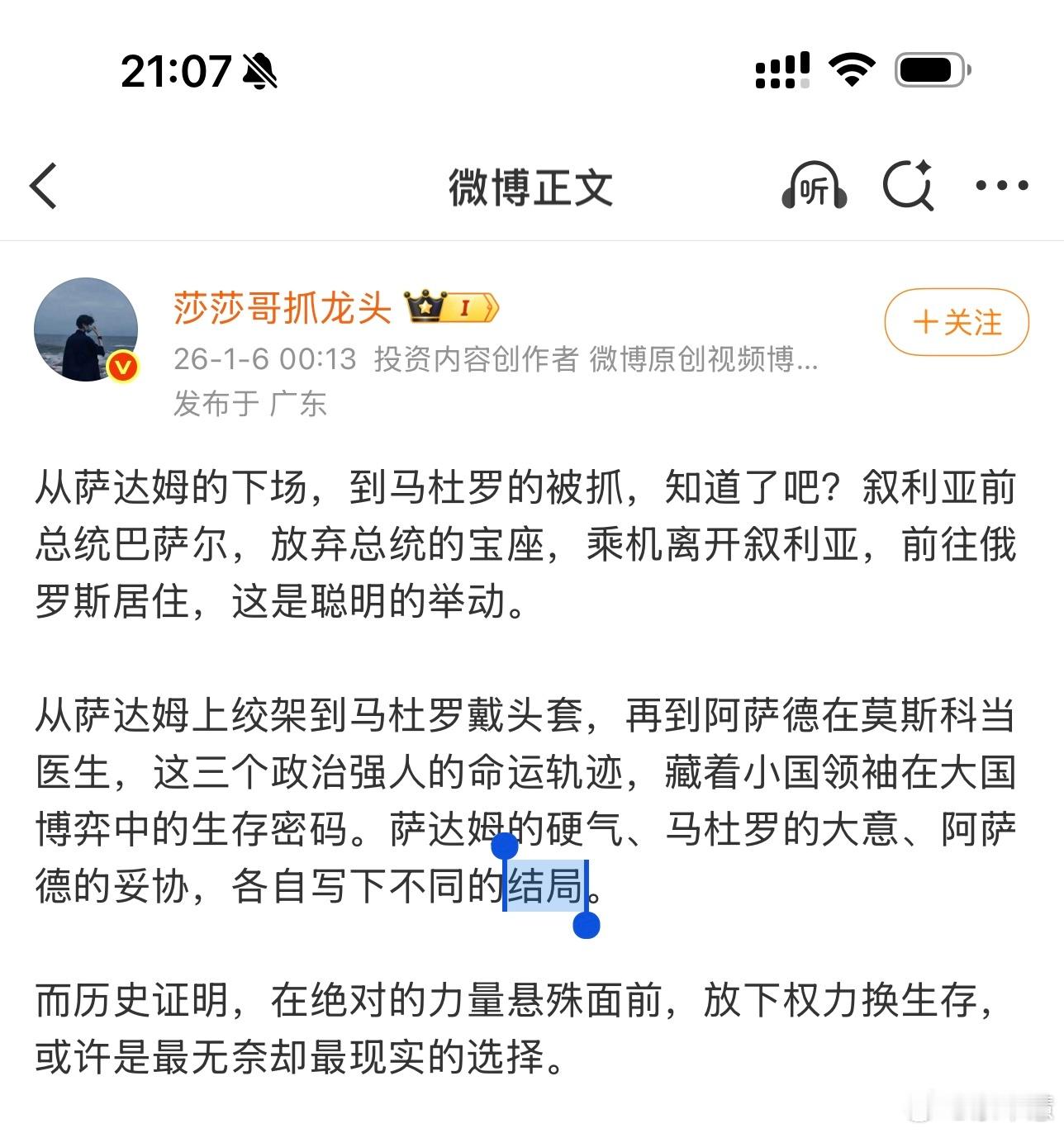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了。 今天整理阳台旧物,翻出个铁皮饼干盒,绿漆掉了大半,边角磨得发亮。打开一看,里面是四十年来攒的粮票、布票,还有张泛黄的结婚照。照片上他穿件灰布中山装,领口别着枚红五星徽章,我扎俩麻花辫,辫梢绑着粉布条,站在供销社门口,身后堆着刚扯的花布——那会儿他说要给我做一辈子新衣裳,扯布的钱还是跟他弟借的。 正对着照片发愣,门“咔哒”开了,是女儿朵朵,手里拎着个玻璃罐,罐口缠着层保鲜膜。“妈,爸让我把这个给您。”她把罐子塞我手里,“他说您换季总咳嗽,这是他托人从老家捎的秋梨膏,熬了整整一下午呢。” 我捏着玻璃罐,罐身还温乎,许是他揣怀里带来的。想起那年冬天我咳得睡不着,他半夜跑三里地敲开药店门,回来冻得耳朵通红,把药揣进被窝捂热了才给我。那会儿多傻呀,就为这点事,记了半辈子好,好像那些摔碗砸盆的日子都没存在过似的。 “他自己咋不送来?”我把罐子搁窗台,阳光照上去,琥珀色的膏体晃悠着,像块凝固的蜂蜜。 朵朵低头抠手指,指甲盖涂着淡粉色指甲油:“他不敢,说怕您烦。上周他去公园遛弯,看见您跟李阿姨跳广场舞,回来跟我念叨,说您穿那件红裙子真好看,比年轻时还精神。” 我忍不住笑了:“他倒是会挑好听的说。”转身从冰箱摸出瓶酸梅汤,倒了两杯,“你爸这些年,就这点没变,嘴甜,可手脚跟不上。以前说给我打个衣柜,木料堆院子里烂成渣;说带我去北京看天安门,到现在我连火车站都没跟他一起出过。” 朵朵猛吸口酸梅汤,吸管“咕噜噜”响:“妈,爸说他知道错了,他把烟戒了,酒也少喝了,退休金卡都给我了,说您要是回去,家里钱都归您管。”她眼睛亮晶晶的,像揣着颗糖的小孩,盼着我点头。 我拿手绢擦了擦照片上的灰,照片里的姑娘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辫子甩得老高。那会儿我以为,日子就是花布衣裳、秋梨膏,还有男人嘴里的一辈子。可过着过着才发现,一辈子太长了,得找个能让你踏实喘气的人,而不是天天提心吊胆,怕哪句话说错就炸锅,怕哪个碗没洗干净就摔桌子。 “朵朵,”我把照片塞回饼干盒,锁进柜顶,“替我谢谢他,秋梨膏我留下了,人就别再惦记了。妈现在挺好,早上遛弯买俩糖油饼,热乎的,咬一口直冒糖渣;下午跟李姐她们跳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跳得比谁都带劲;晚上看两集电视剧,不用等谁回家,不用听谁咳嗽,多踏实。” 朵朵没再劝,只是走的时候,偷偷往我枕头底下塞了张纸条,上面是她爸歪歪扭扭的字:“我种的月季开了,红的,跟你当年那件裙子一个色。” 我捏着纸条笑了,月季开得再好,也不是我的花了。窗台的秋梨膏在风里飘着甜香,像极了那年冬天的味道,可我知道,有些味道,闻闻就够了,不必再尝第二遍。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了,六十多岁的人了,日子得往前过,不能总回头看,您说对吧?
上夜班回来的丈夫,看见妻子没有做饭,反而在大口大口的吃榴莲,丈夫气不打一处
【2评论】【2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