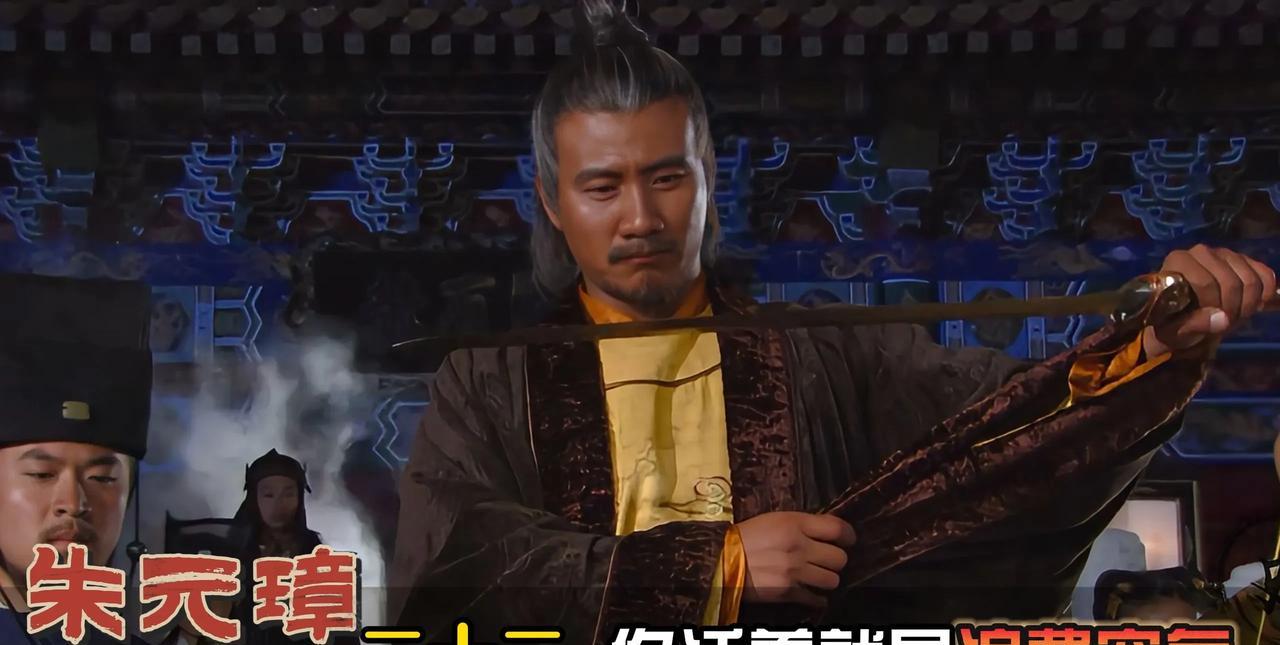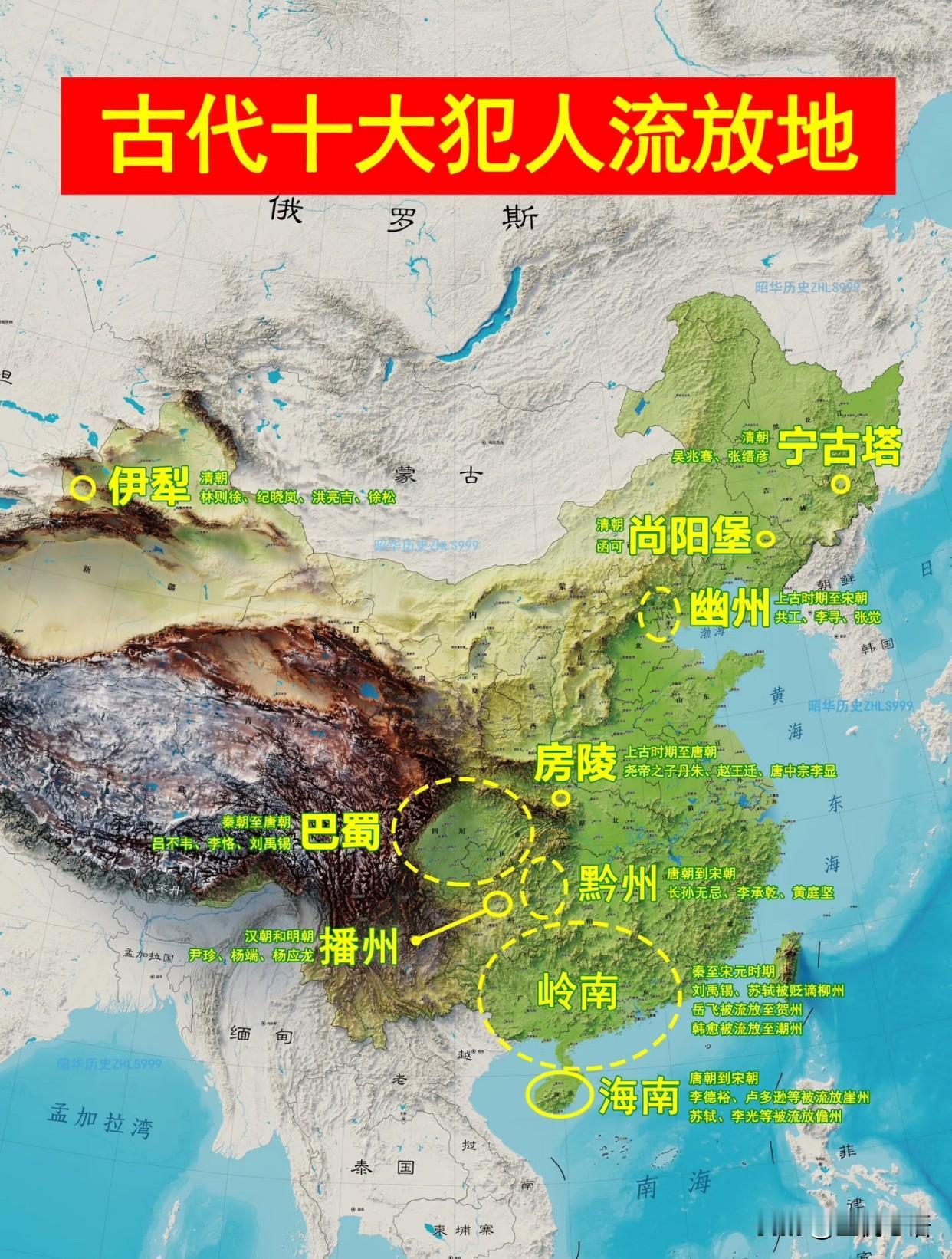[太阳]1997年,48岁的耿保国不顾家人反对,借遍亲朋好友又咬牙贷款几十万,终于凑够了100万买下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明清古宅,此后他又把后半辈子的时间,都放在了修缮复原这座老宅上面。 (参考资料:2018-10-08 新湖南——电影《1942》中的这座院子,竟是70岁老人苦修20年的坚守) 在商家扎堆的平遥古城,藏着一个3000平米、70间房的“异类”,它不卖票,也不做景点,更像一个活物,靠着艺术的滋养,顽固地抵挡着周围的商业浪潮。 它的守护者叫耿保国,一个穿布鞋、腰上挂串钥匙的老头,你很难说清他到底是院子的主人,还是它身上一个不可或缺的“器官”。 这座大院的来头不小,建于明末清初,比名声在外的乔家大院还早250年,它的第一任主人,是当年中国首家票号“日升昌”的大掌柜冀玉刚,三进两院过道厅,完全是四品官的规制,底子硬得很。 可到了1997年,它几乎就是一片废墟,屋顶的草长了半人高,那年平遥正在申遗,政府却穷得没钱修,只好拿出来拍卖,看热闹的多,真掏钱的没几个。 48岁的耿保国,一个一辈子跟漆器打交道的手艺人,当时还租着房,却用半生积蓄加上贷款借款,凑了100万,把这院子拿下了,全家都炸了锅,弟妹们更是担心,这房子以后会不会被收回去。 可耿保国不管,他骨子里有种手艺人对老东西的疼惜,修复,不是装修,更像一场跨越400年的对话,院子原先的门楼早就毁了,他没随便造一个,而是花了四五个月,跑遍了当地几百个门楼,亲手画出图纸,让它“长”回了原来的样子。 为了让新修的部分不显得突兀,他坚持“修旧如旧”,专门跑去乡下搜罗明清时期的旧砖瓦和石雕,光是一个给他干活的木工老师傅,就跟着他干了二十多年,这院子,就是这么一点点被重新“养”起来的。 最绝的是主院正房那块“高山仰止”的匾额,从书法到设计再到雕刻,全是他一个人包了,光是为写好那四个字,他就足足练了15年,他这是把自己的修为,刻进了院子的骨头里。 这么大的院子,二十多年的修复,前前后后砸进去四五百万,钱从哪来?答案全在耿保国和他儿子的手上——卖漆器,这院子的生存逻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闭环:创作,卖钱,再投进院子里,院子的呼吸节奏,完全跟着艺术品的诞生频率走。 他们拒绝了所有把商业引流进来的机会,有人劝他在临街开个店,生意肯定火,他不去,怕儿子们闻惯了钱味儿,忘了怎么做艺术家,如今,父子俩就在院里辟个小角落卖作品,两个儿子轮流看店,各卖各的,收入也归自己。 如今,院子里空着的房间,顺理成章地成了父子俩的私人美术馆,空间滋养了艺术,艺术又用卖画的钱,反过来维持着这个巨大空间的存在。 这院子的高墙,不只挡住了风沙,更挡住了外面世界的各种诱惑和算计,当年导演冯小刚想借院子拍《1942》,提出要局部改造,耿保国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在他眼里,这院子是个完整的生命,动哪儿都不行。 还有领导建议他,干脆把这70间房改成宾馆,生意绝对好。耿保国听完直摇头,说那得建70个厕所,自己不就成了毁坏文物的“罪人”?这是一种近乎偏执的守护,也是一种清醒的底线。 这种价值观,也深深烙印在了他对自己儿子的教育上,儿子拿了全国金奖,他却严厉禁止孩子去参评什么“工艺大师”的头衔,他总说,作品好才是真本事,虚名没用。 现在,一家四口就住在这3000平米的大院里,外人看来或许有些冷清,但他们自己却觉得无比安宁,钱够用就行,太多了只会把人累死。 1997年,耿保国买下了一座破败的古宅,所有人都觉得是他拯救了这院子,可二十多年过去,回头再看,或许更是这座院子,用它400年的厚重与沉静,守护住了一个手艺人家庭最宝贵的艺术理想。 耿保国和他腰间那串叮当作响的钥匙,守的不是一处房产,而是一种快要消失的“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