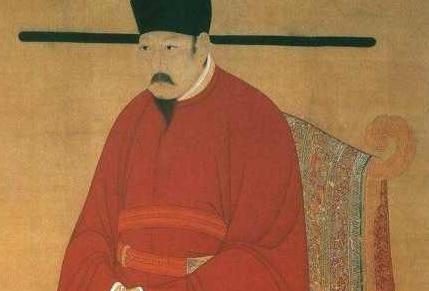857年,唐宣宗看中了新科进士王徽,想招他为驸马。王徽赶紧跑到宰相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我今年都40岁了,身体也不好,实在是高攀不上公主啊。”宰相扶额长叹:这已经是第三个拒绝娶公主的人了! 大明宫里,唐宣宗看着新科进士的名录,最终盯住了“王徽”二字上。 这位年近四十的进士,刚在殿试中因策论“切中时弊”被圈为前三。 此刻却跪在宰相令狐绹府前,涕泗横流。 “徽年逾不惑,体弱多病,若尚公主,恐辱没皇家天眷!” 这是今岁第三个哭求“逃婚”的新科进士。 令狐绹叹了口气:“前有于琮托病辞官,后有郑颢千里追妻。” 话音未落,殿外小太监来报:“宣宗爷传旨,问王进士可愿再考虑?” 其实,王徽的恐慌,并非无由。 半年前,宣宗为三女儿永福公主选驸马,相中了新科进士于琮。 于琮出身寒门,苦读二十年才中进士,接到圣旨时腿都软了,连夜写奏疏推辞:“臣门第微贱,不敢攀附帝女。” 宣宗暂且搁置,却在次年改主意。 他将广德公主许配于琮,却不想永福公主在御前摔了玉筷:“这般酸儒,也配做我驸马?” 更早的先例是郑颢。 这位状元郎本与范阳卢氏女有婚约,宣宗硬要招他为驸马,派宰相白敏中快马追回。 郑颢被迫尚主后,终身记恨白敏中,晚年被贬时还在奏疏里写:“唯此事,臣愧对平生所学。” 如今轮到王徽,他比谁都清楚:娶公主不是“平步青云”,是“自缚手脚”。 但是,为何士子们谈“驸马”色变? 首当其冲是公主的性子。 唐代公主地位尊崇,自小锦衣玉食,多有骄纵。 永福公主摔玉筷是明证,更早的太平公主更甚。 她在府中设“公主府衙”,私养门客,甚至干预朝政,最终因谋反被赐死,夫家薛氏满门获罪。 安乐公主更狂,曾蒙住诏书逼唐中宗盖章,还想效仿武则天称帝,最终被李隆基斩杀。 这些前车之鉴,让士大夫们心有余悸。 正如时人谚语:“娶妇得公主,平地生公府。” 娶了公主,便等于在家中供了尊“活菩萨”,稍有不慎便家破人亡。 其次是驸马制度的“隐形枷锁”。 唐代为防外戚干政,明文规定驸马不得任三省要职,不得参与核心政务。 宣宗的大女婿郑颢,本是状元之才,却因尚主,一辈子没当上宰相。 另一位驸马郭暧,虽因“打金枝”出了名,最终一辈子都困在闲职上。 对苦读的文人来说,科举是改命的梯子,驸马身份却是梯子上的断木。 王徽哭着说:“我连风寒都常犯,惹了公主怕是连命都保不住,还谈什么光耀门楣?” 更深层的矛盾,藏在士族的“面子”里。 安史之乱后,唐代士族虽遭冲击,仍以“门第清贵”自矜。 山东旧族如崔、卢、李、郑、王诸姓,互通姻娅,视“皇家女婿”为奇耻大辱。 时人用“禁脔”代指驸马。 士家大族都认为驸马这身份就是皇家豢养的“珍味”,与凭借才学立身的士人风骨相悖。 唐文宗曾愤怒质问:“我家做了二百年天子,难道还比不上崔、卢两家?” 可士族根本不买账。 他们宁可与同等级的旧族联姻,也不愿尚公主失了清望。 面对士子们的集体“逃婚”,唐宣宗并非不知症结所在。 他曾下诏告诫万寿公主:“莫轻视夫家,莫干涉时事”,甚至让她乘铜饰车舆以示节俭。 可皇权威严让他难以接受“金枝玉叶没人要”,曾质问宰相:“我的女儿都是尊贵之身,为何不如民间女子抢手?” 刘瑑硬着头皮回话:“陛下,士子怕的不是公主,是丢前程、没尊严啊!” 宣宗最终没强迫王徽。 他被调去吏部任职,后来官至尚书,在乱世中做了不少实事。 而被选中的于琮,虽因广德公主的贤淑得了善终,却也成了晚唐最特殊的“驸马样本”。 大中十一年的这场“逃婚风波”,表面是新科进士避婚,实则是晚唐皇权与士大夫理想的激烈碰撞。 公主的娇贵、驸马的枷锁、士族的清望,层层叠叠织成网,困住了宣宗的“皇家姻缘”,也困住了士子的“致君尧舜”梦。 正如史家评:“唐室之衰,非一日之寒;驸马之惧,实万机之弊。” 王徽后来在笔记里写:“幸未尚主,否则一生困于金笼。” 这句话,道尽了那个时代读书人的挣扎。 他们能忍十年寒窗,能熬宦海沉浮,却不愿用理想换一顶“驸马都尉”的虚冠。 有些枷锁,比贫穷更可怕,有些选择,比荣耀更珍贵。 主要信源:(凤凰网——唐宣宗想招新科进士为驸马,进士宁辞官不愿娶,还跑去找宰相哭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