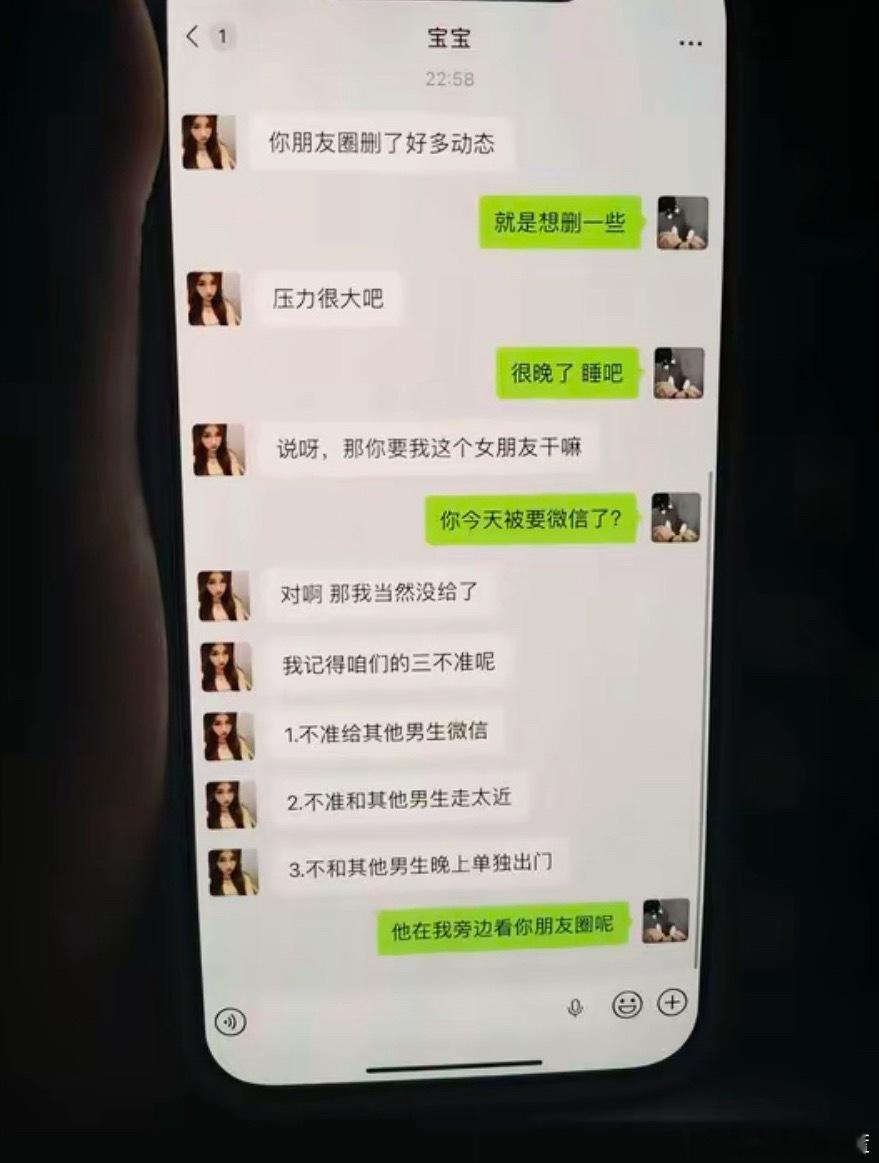1994年,太原一女婴因手臂残疾被抛弃,58岁拾荒妇人见其可怜,把她捡回家用面糊糊养大,高思恩为了省车费,每天跑步5公里去上学。谁料,因此跑出了不一样的人生。 58岁的拾荒妇人哪有什么积蓄,天不亮就挎着破布袋子出门,沿着巷弄扒拉垃圾桶里的纸壳、塑料瓶,换回来的钱攥得皱巴巴,先匀出大半买最便宜的面粉。熬面糊糊的时候,她总把锅里最稠的那碗盛给高思恩,自己就着锅边刮点稀汤,配着硬邦邦的窝头咽。 高思恩刚懂事儿就摸得清家里的光景,看着奶奶手背皴得裂了口子还在捡废品,攥着奶奶给的车费钱,脚刚迈出家门又缩了回来——那几块钱够买小半袋面粉,她咬咬牙,把钱塞回奶奶的口袋,说“我跑着去学校,锻炼身体”。 从家到学校的5公里路,她每天来回跑,天刚蒙蒙亮就出门,冬天呼出来的白气裹着冻红的脸,棉鞋磨破了边就垫块旧布接着穿; 夏天汗珠子砸在柏油路上,后背的衣服湿了又干,结出一层白花花的盐渍。她没喊过累,跑的时候总攥着拳头数步子,心里念着奶奶留在灶台上的那碗面糊糊——那是她一整天的劲儿头。 有时候跑到学校腿都发颤,她就靠在教室外的墙根儿喘口气,等劲儿缓过来了再进去上课,课本里的字都透着暖,因为她知道,好好学才能对得起奶奶熬面糊糊的苦。 奶奶没读过书,却总在夜里坐在床沿,摸着她残疾的那只胳膊说“咱不比别人差,好好跑、好好学,以后能过饱饭的日子”。这话没什么华丽的词,却像根绳子,把高思恩的心思拴得紧。 她知道奶奶捡废品的腰越来越弯,知道家里的面袋空了又空,所以跑步的时候更卖力气,学习的时候更较真——课上没听懂的知识点,她能追着老师问半节课;课后的作业,她趴在昏暗的灯泡下写得工工整整,连笔画都不肯潦草。 跑着跑着,学校的体育老师注意到她。别的孩子跑两圈就捂着肚子喘气,她跟着跑五圈还能稳住气息,步频匀得像刻好的钟。老师拉着她问是不是练过,她摇摇头说“就是每天跑着上学省车费”。 后来老师推荐她进了学校的长跑队,不用再自己挤时间跑,队里还发了合脚的运动鞋——那是她长这么大,第一双没补过的鞋。她把旧棉鞋收进书包最底层,每次穿上新鞋跑起来,都觉得脚步轻得能飘起来,那轻里裹着的,是奶奶没说出口的盼,是自己攥了好多年的劲儿。 她没因为手臂的残疾露过半分怯。长跑队里训练,别人能用两只手系鞋带,她就低着头,用那只健全的手慢慢系,系得比谁都紧;比赛的时候,她攥着拳头往前冲,残疾的胳膊晃在身侧,却比谁都跑得快。 连对手都盯着她的背影愣神——没人知道,这背影背后,是无数个啃着凉窝头的清晨,是无数碗稠稀分匀的面糊糊,是奶奶皴裂的手和那句“咱不比别人差”。 后来,她靠着长跑特长和拔尖的成绩考上了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她攥着纸跑回奶奶的破屋子,把通知书拍在刚熬好的面糊糊锅边。 奶奶的眼泪砸在纸面上,晕开了“录取”两个字,她一边擦奶奶的泪,一边说“以后我能挣工资,您不用捡废品了,咱每天都能吃稠面糊糊”。那天的面糊糊里,奶奶偷偷加了半勺糖,甜得高思恩皱起了眉,又笑着咽了下去——那是她长这么大,吃过最甜的一碗面糊糊。 进了大学,她没停下跑。跑道从家门口的土路换成了大学的田径场,她不仅在赛场上拿了奖,还靠着兼职和奖学金,给奶奶租了带暖气的小房子,买了软和的棉服。奶奶不用再天不亮出门拾荒,能坐在窗边晒着太阳织毛衣,只是每次看见高思恩跑步回来,还会端上一碗热乎的面糊糊,说“跑累了,喝点稠的”。 这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传奇,是一个拾荒奶奶用面糊糊攒出来的盼,一个残疾女孩用5公里的脚步踩出来的路。那些熬出来的苦、跑出来的汗,到最后都成了托着人往上走的劲儿——只要肯攥着对在乎的人的体谅,肯咬着牙往前挪,再难的日子,都能跑出亮堂的活法。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