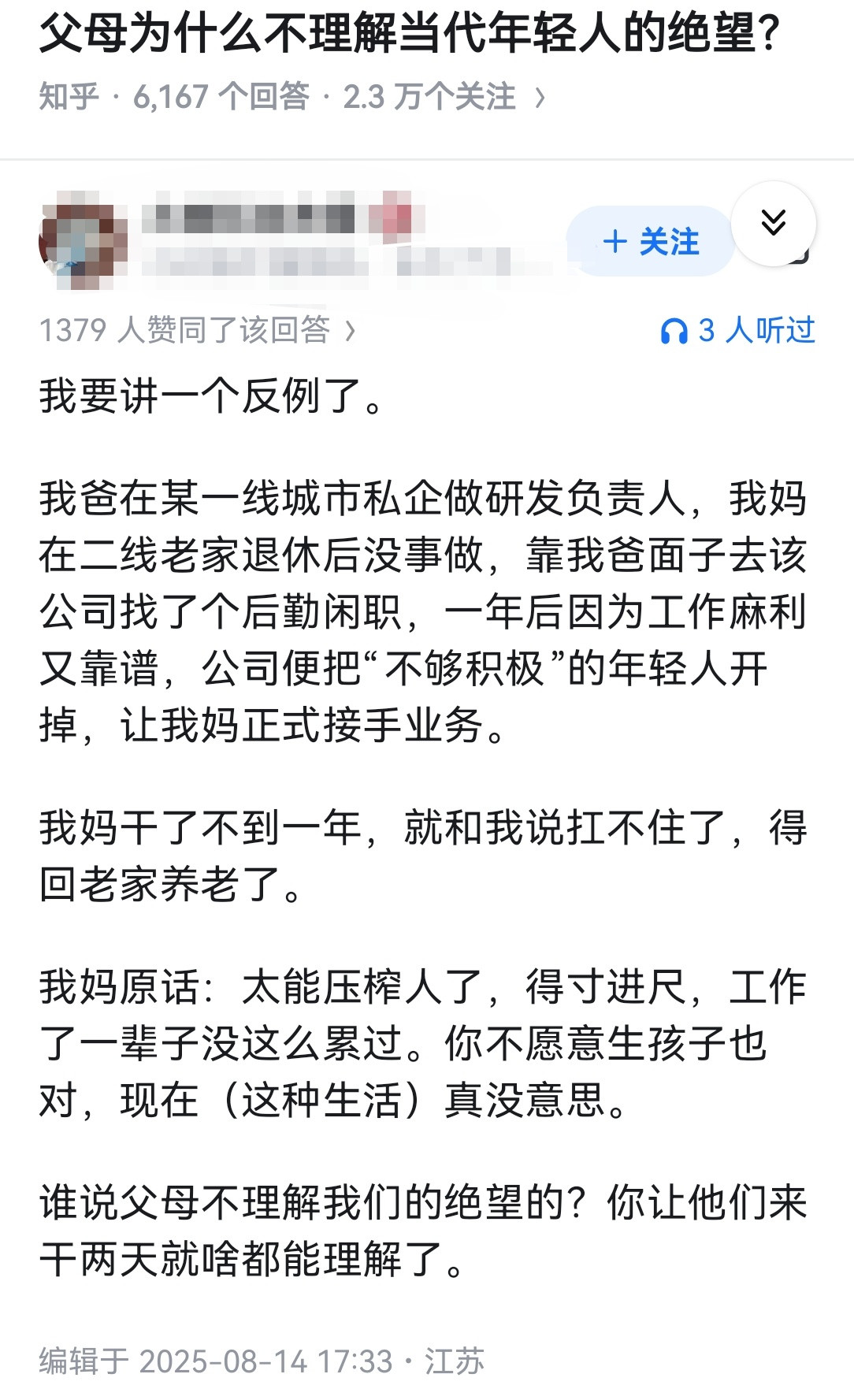1967年正月初六早上,张恨水在包油条的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随后脸色苍白,手微微颤抖。次日,家人为张恨水穿鞋时,却发现他已因突发脑溢血离世。 当那位掌管水利的厅长气势汹汹地找上门,质问为何对市面上泛滥的盗版书视若无睹时,张恨水的回答出人意料的犀利:“我只恨你”对方错愕不解,他才慢悠悠地补上一句:“你管水,我是恨水,我不恨你恨谁”。 这句玩笑话背后,藏着的却是一份少有的通透:如果那些身处穷乡僻壤、甚至有些寒酸的读者能从盗版书中窥见一丝光亮,汲取几分慰藉,他又何必去计较那点版税,这份狂狷与慈悲并存的底气,源自他笔下那个浩瀚的文字江湖。 作为民国通俗小说的扛把子,他的产出量大得惊人,全集字数逼近三千万,中长篇写了一百二十多部,就连西方的快枪手巴尔扎克、大仲马凑在一起,在产量上也未必能压他一头,但张恨水并非只会写风花雪月,他其实是文坛里最独特的“武林高手”。 鲜少有人知道,这位以言情闻名的文人,骨子里流淌着的是武将的血,祖父是当年湘军的参将,功夫深不可测,一双筷子能随手夹住飞舞的苍蝇,父亲也是条硬汉,曾遭千人围堵却能全身而退。 幼年的张恨水,没少骑着家里的山羊假装千里马,挥舞着祖父特制的竹刀竹剑,做着策马江湖的梦,那把纳鞋底的锥子,曾被严母用来随机扎透古籍,考校他能不能将扎中之处倒背如流,正是这种近乎严苛的童年特训,练就了他日后左手打麻将、右手写连载。 剧情还在脑子里如脱缰野马般奔腾的“绝世武功”然而,现实的江湖远比小说残酷,父亲的突然病故,让他从“愿学祖父佩长剑”的少年,瞬间跌入“穷在闹市无人问”的困顿,那个本来打算出国留学的剪辫青年,被迫在人情冷暖中早早成熟。 为了糊口,他在报馆里身兼数职,取南唐李后主“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意,化名“愁花恨水生”谁能想到,这个带着几分颓唐与酸楚的笔名,日后竟成了从弄堂妇孺到政坛大佬都绕不过去金字招牌。 他的读者圈子奇特地打破了阶层壁垒,一边是章士钊、陈寅恪这样的顶级学者,哪怕眼睛快看不见了,还要听人念他的《水浒新传》另一边是政治场的风云人物,据说蒋介石特意登门,张学良甚至开出百元大洋的高薪想聘他做顾问。 更别提那在书摊前排队购买的鲁迅,以及不仅爱读还深受其影响的才女张爱玲,就连那狂傲的老舍,也心悦诚服地送了他一顶“国内唯一妇孺皆知”的帽子,但若是只把他看作是个写鸳鸯蝴蝶派的畅销书作家,那便太小看张恨水了。 当“九一八”的炮声震碎了旧梦,他的笔锋陡然一转,变得比刀剑还要犀利《满城风雨》里,他不再写才子佳人,而是将军阀的残暴与日寇的贪婪撕扯开来,把义勇军的殊死抵抗刻进字里行间。 1944年,他更是不取分文,满怀激愤地为57师那些视死如归的战士立传,这部以此血泪写就的作品,甚至在硝烟中意外促成了一段苏州闺秀与抗日师长的战地姻缘,从流亡重庆的积劳成疾,到定居北京的晚景沉思,这位写尽了悲欢离合的老人。 自己的结局却充满了令人唏嘘的宿命感,1967年的正月,北方的冬天冷得刺骨,大年初六的清晨,张恨水正准备吃早餐,那包裹着两根油条的旧报纸上,一行字猝不及防地撞进了他的眼帘:老舍,那位曾与他惺惺相惜、盛赞他为“唯一”的好友,竟投湖自尽。 没人知道那一刻他想了什么,是想到了昔日排队买书的盛况,还是那片埋葬了无数文人风骨的太平湖,仅仅一天之后,在家人躬身为他穿鞋的那个清晨,七十二岁的张恨水突发脑溢血,在一个无声的早晨,就这样把自己永远留在了昨天。 那个曾经鲜衣怒马、恨水长东的“天字第一号”说书人,最终以最沉默的方式,为那个时代画上了一个仓促而悲凉的句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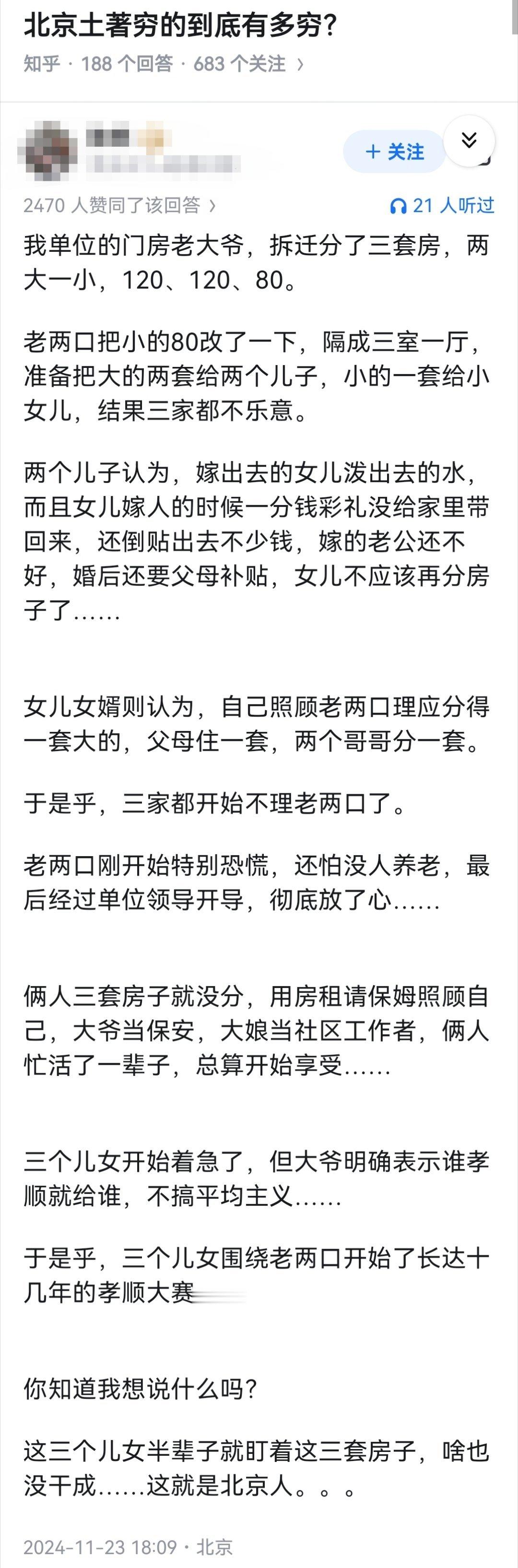
![小小举动太暖心了!真的让人泪流满面[哭哭]太好哭了[哭哭][哭哭]昨晚上的比赛,](http://image.uczzd.cn/10913497019102117337.gif?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