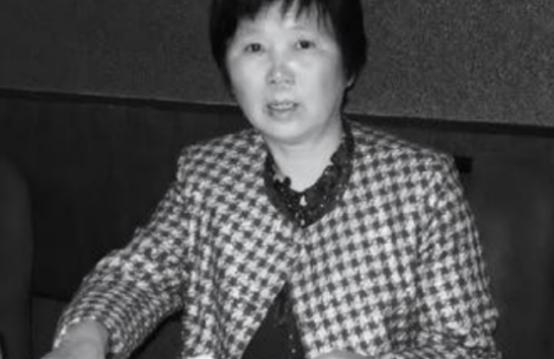1974年,21岁女知青,夜间独自去厕所,却神秘失踪,连队把整座山翻了个遍,却仍然找不到人,直到2009年,老知青们在聚会时,在沙发上抽烟的老知青突然问了一句:你们说,小朱有没有可能是自己走的? 1970年,上海姑娘朱梅华响应号召离开城市,来到云南西双版纳东风农场当知青。她出身普通工人家庭,会画画会跳舞,性格开朗,很快成了连队里的文艺骨干。 白天挥锄开荒种橡胶,晚上唱歌跳舞给大家解闷,很多知青都说有她在,连队的日子就亮堂一些。 东风农场环境艰苦,住的是潮湿茅草屋,墙角虫蚁成群,雨季泥泞难行,蚂蟥往腿上钻,蚊虫在耳边团团转。 刚来时,朱梅华写信回家,说要在边疆建功立业,争当先进。但一年年过去,体力劳动的消耗和精神上的落差,慢慢磨掉了她的热情,话变少了,文艺活动也不怎么参加。 一九七三年,她曾回上海探亲,一见到母亲就大哭,说不想再回去了。家人却劝她再坚持,说既然是国家安排,就不要半途而废。 春天一过,她又回到西双版纳,回到潮湿闷热的胶林里。此后她更沉默,只把母亲送的那块手表一直戴在腕上,仿佛紧紧攥着和故乡最后的一点联系。 一九七四年四月初的一天夜里,西双版纳暴雨如注,雷声在山谷间滚动。半夜,朱梅华被憋醒,起身想上厕所,先推了推同屋刘桂花,对方困得睁不开眼,含糊推辞。朱梅华只好自己拿着火柴,顶着大雨走出宿舍,顺着通往厕所的泥路消失在黑夜中。 第二天早晨点名时,她的铺位空着。室友回屋一看,被褥叠得整整齐齐,衣物都在,人却不见了。 连队立即组织大搜寻,从厕所一带往山林河岸一路排查,在泥地里看到几处模糊脚印,最后在通往另一连队的岔口,发现了一只沾满红土的黑布鞋,大家一眼认出是她的。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新线索。 连队只好向上级和当地公安报告。随后,兵团和公安抽调人手,翻山越岭找了好几周,树林山坡河滩都摸过,连几处新翻的土堆也挖开查看,还带来军犬搜索。 有人猜她趁夜偷渡去了不远的边境,边防也核查过,却没有任何记录。这条路很快断了。 在没有尸体没有目击者的情况下,侦查只能从她身边的人查起。首先被盯上的,是和她关系暧昧的男知青祝为鸣,两人从上海同来边疆,后来闹过矛盾,有人说在他搪瓷杯底压着一张写有烧死朱梅华字样的小纸片。 他被多次审讯,承认吵过架,却一直否认当晚外出,也找不到能证明他作案的物证,最终只好暂时排除。 另一名重点嫌疑人是连队指导员蒋金山。他住在女宿舍对面,有家暴猥亵前科,常被人质疑举止不规矩。 案发当晚他回家时裤脚满是泥,妻子还替他洗过一件女式衣服。调查组搜查他家时,在墙缝里翻出一块女式手表,样式和朱梅华平日佩戴的十分相似。他一度承认和案件有关,又很快翻供,甚至多次变换所谓埋尸地点。 几处地方挖下去都毫无发现,最后他只因其他性侵行为被判刑,和这宗失踪案始终没能形成完整证据链。 随着时间推移,搜寻和调查渐渐冷下来。朱梅华的父母从上海赶到西双版纳,拎着女儿的相册和画册,挨个问知青有没有见过她最后一面,得到的只有摇头叹息。 此后许多年,每到清明,母亲都会往农场寄去包裹,里面是女儿爱吃的五香豆和几句盼你平安的问候,包裹一次次原封退回。 到了二十一世纪,老知青重聚时,这个名字仍被反复提起。有人坚信她早已死于那场雨夜,只是尸骨再也找不到,有人宁愿相信她凭着一腔执拗逃离了农场,绕过巡逻去了遥远的另一边。 所有猜测都缺乏确证,这桩发生在雨林深处的旧案,就这样被时间封存在记忆里,成了一个再也无法完全还原的知青时代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