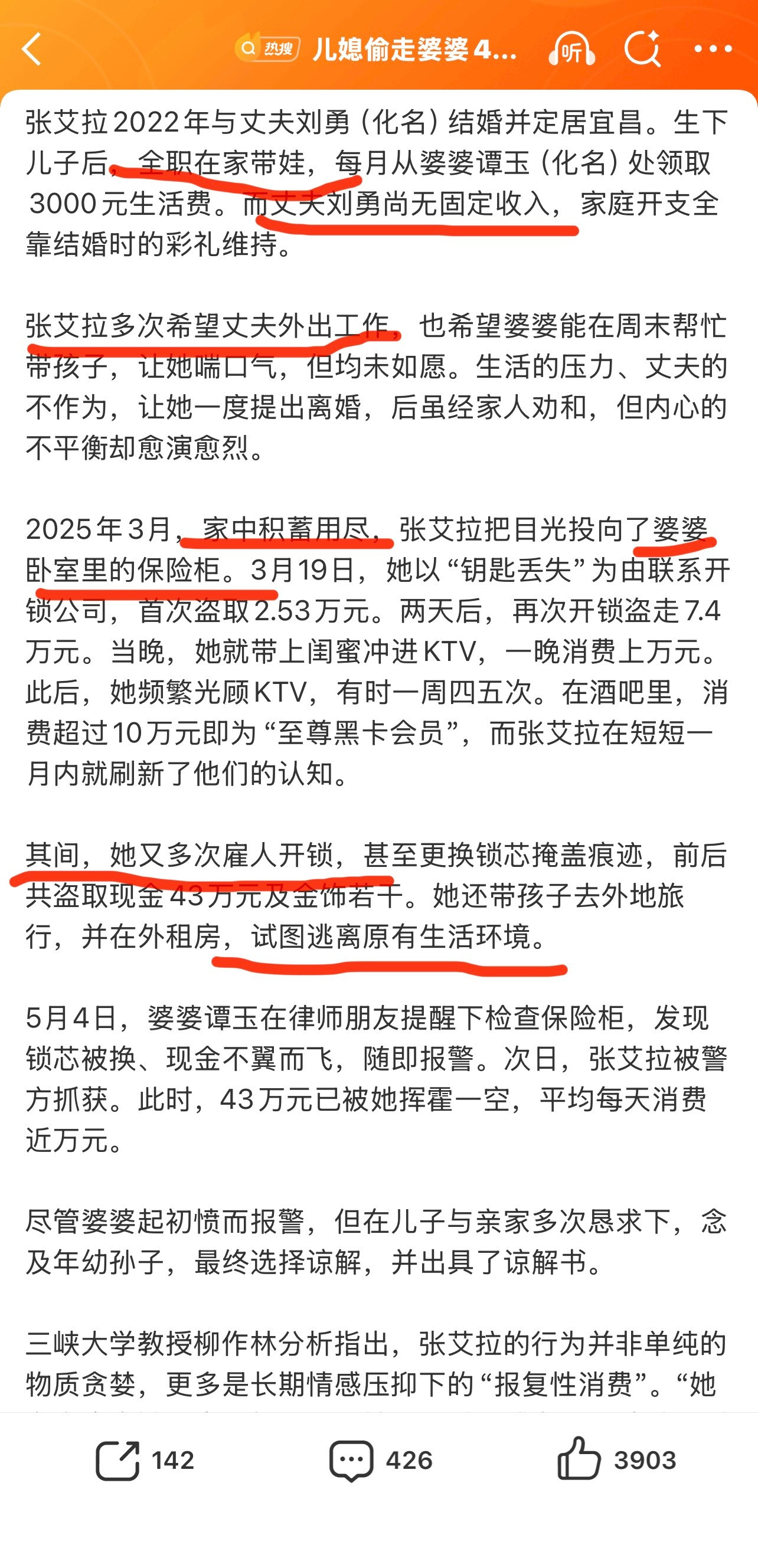有一份体制内的工作,你会发现,你的工资一个月只有三四千块,不管再累,不管再努力,但是你却绝对饿不死。老周常把这话挂在嘴边。他在街道办干了十五年,从青涩小伙熬成了两鬓带霜的“周哥”,办公桌抽屉里永远躺着半包最便宜的烟,茶杯底结着层深褐色的茶垢。 街道办三楼的格子间,日光灯管总在下午三点发出嗡嗡的轻响。 老周坐在靠窗的位置,背对着走廊,后颈的头发里藏着几根白得刺眼的银丝——那是十五年光阴最诚实的戳记。 “有份体制内的工作,你就发现,工资就三四千,再累再努力,饿不死。”这话他常说,说的时候总拿指节敲敲桌面,像是在跟自己较劲,又像是在给空气交底。 办公桌抽屉半开着,露出半包“红塔山”,烟盒边角被手指磨得起了毛边;旁边的搪瓷茶杯,茶垢结得厚,阳光斜照进来,能看见里面沉着片泡得发白的枸杞。 新来的大学生小王第一天报道,就听见老周跟隔壁科室的李姐说这话。 他偷偷打量这个“周哥”:衬衫领口松垮,裤脚沾着点早上骑电动车带的泥点,说话慢悠悠的,连翻文件都带着股不慌不忙的劲儿。 “周哥,您在这儿十五年了?”小王递过去刚泡的茶,想套近乎,“外面公司招行政,月薪八千起呢,您……” 老周没接话,先把茶杯接过去,用杯盖刮了刮浮沫,茶垢在水面荡开一圈圈褐色的涟漪。 “饿不死,”他重复了一遍,这次声音轻了点,“但也冻不着,冻不着那些等着我的人。” 小王没听懂,只当是老周安于现状,心里暗笑:这大概就是传说中“混日子”的体制内老人吧。 直到上个月那场暴雨。 下午五点,雨点子砸在玻璃窗上噼啪响,天气预报说有雷暴,大家都急着收拾东西下班。 老周却突然站起来,从抽屉最里面翻出个皱巴巴的笔记本,又把那半包“红塔山”塞进裤兜,抓起墙角那把伞骨断了一根的黑伞就要往外走。 “周哥,您去哪儿?”小王喊住他。 “三号楼张奶奶,”老周头也不回,“她关节炎犯了,今天该换药贴,早上打电话说家里的用完了,我得给送过去。” 小王愣住了——张奶奶?他来俩月,只在档案里见过这个名字,老周怎么连她哪天换药都记得? 那天雨下得像要把整个街道淹了,老周披着件洗得发白的雨衣,踩着积水深一脚浅一脚地往三号楼走,手里还攥着那把断了骨的旧伞——那是张奶奶上次来办事忘在这儿的,他说“老人家眼神不好,丢了又得心疼好几天”。 小王鬼使神差地跟了上去,躲在单元楼门口的屋檐下,看见老周在张奶奶家门口蹲了半小时,帮老人贴好药贴,又弯腰把门口的积水扫进下水道,临走前还摸出手机,调大音量给老人放了段越剧。 “您慢点走,周同志!”张奶奶在门里喊,声音亮堂得很。 老周摆摆手,转身往回走,雨衣帽子滑下来,露出额角的水珠,也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汗。 路过花坛时,他掏出那半包“红塔山”,抖出一根叼在嘴里,却没点,手指在烟盒里摸索了半天,摸出张折叠的纸条——小王后来才看清,那是张手写的居民联系表,上面密密麻麻记着谁家住几楼、谁有高血压、谁家孩子放学没人接。 原来那半包烟不是用来打发时间的,是他走街串巷时,跟修鞋的老李、看大门的王伯递烟聊天的“敲门砖”;原来那结着茶垢的茶杯,每天早上都泡着枸杞,是因为总有人来办事时顺手放下两颗,说“周哥你天天操心,补补”。 “饿不死”的工资,养着的何止是他自己? 是张奶奶膝盖上的药贴,是老李摊位上那把总修不好的旧伞,是放学路上等他接的三年级小孩手里的棒棒糖。 你说,这世上的安稳,是不是都藏在这样“饿不死”的日子里,藏在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坚持里? 小王突然想起老周说“冻不着那些等着我的人”时,手指在茶杯沿摩挲的动作——那不是麻木,是把十五年的琐碎,磨成了心里的秤,秤砣是责任,秤盘里是街坊四邻的日子。 第二天早上,小王帮老周洗茶杯,茶垢泡软了,用抹布一擦就掉,露出底下搪瓷的白。 老周看见,眯着眼笑:“哟,新同志就是勤快。” 小王没说话,默默把洗干净的茶杯放在他桌上,旁边摆了包新的“红塔山”——这次,烟盒里夹着的,是他昨晚熬夜整理的新居民登记册。 日光灯管还在嗡嗡响,老周拿起茶杯,喝了口热茶,杯底映着窗外的天,蓝得很干净。
有一份体制内的工作,你会发现,你的工资一个月只有三四千块,不管再累,不管再努力,
昱信简单
2025-12-13 23:50:07
0
阅读: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