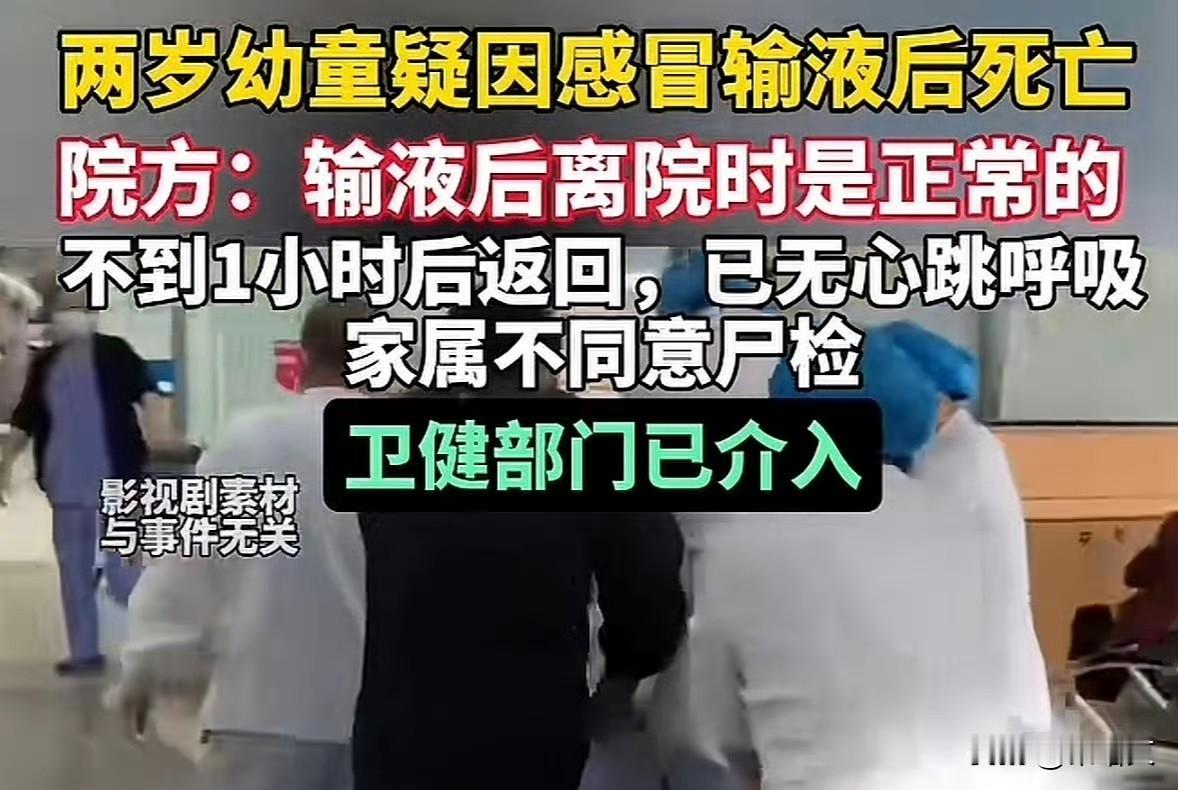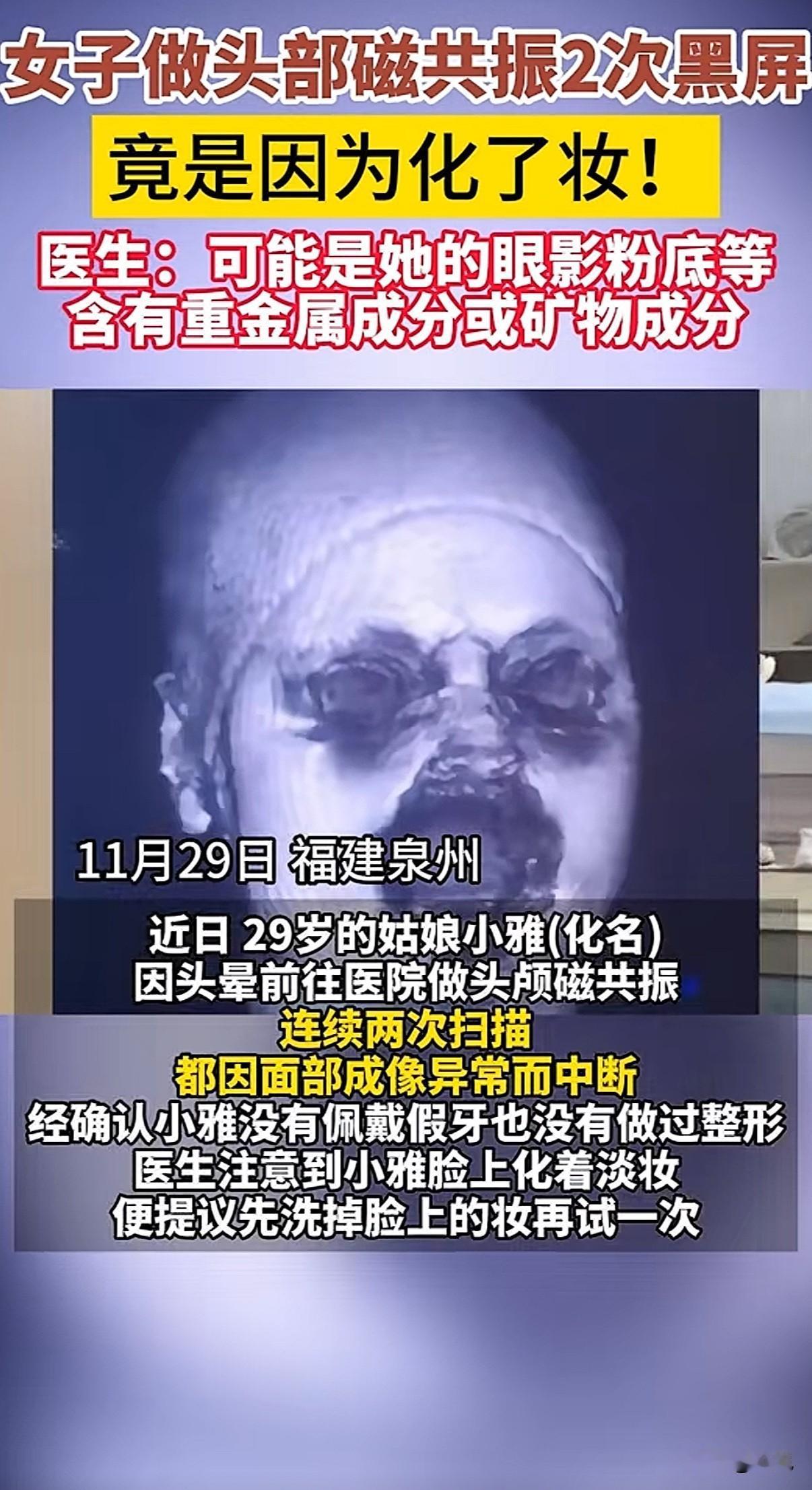我姐45岁非要生二胎,昨天刚生了个儿子,姐夫在病房门口蹲着眼圈都红了,哪有半点当爹的欢喜?去年我就劝她,四十好几了,头胎儿子都上初三了,别折腾生二胎,她偏不听,说就想要个女儿凑“好”字,怎么劝都没用。 昨天清晨的医院走廊,消毒水味混着初秋的风,往人骨头缝里钻。 我提着保温桶拐过护士站时,正看见姐夫蹲在病房门对面的长椅边。 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夹克,背脊弓着,像被什么东西压弯了似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裤缝,眼睛盯着地面,那圈红从眼角漫到颧骨,倒像是刚哭过一场——可昨天护士明明笑着报喜,说姐姐生了个七斤二两的大胖小子。 我站在原地没动,心里直冒问号:这哪是添丁的欢喜? 去年这时候,我还在她家客厅磨破嘴皮。姐姐窝在沙发里,怀里抱着暖水袋,脚边蜷着初三的大外甥,电视里放着狗血剧,她突然转头说:“我想再生一个。” “姐,你都四十五了,大宇明年就中考,你折腾这干啥?”我差点把手里的茶杯洒了。 她没看我,手指抠着暖水袋的花纹:“想要个女儿,凑个‘好’字。” 怎么劝都没用,我说高龄产妇风险大,她说现在医学发达;我说大宇都快比她高了,她说孩子大了家里冷清。 直到昨天进产房前,她还抓着我的手笑,说“要是个闺女,就给她扎小辫,穿花裙子”。 可护士抱出来的是个儿子,皱巴巴的小脸,闭着眼哭得惊天动地。 姐夫就那么蹲着,从护士报喜到现在,一个多小时了,没挪过窝。 “她从凌晨疼到下午,”我终于走过去,听见他的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医生说差点大出血,签同意书的时候,我手抖得笔都握不住。” 我突然想起去年劝她时,她摸着小腹笑的样子,说“大宇小时候多可爱,再生一个,家里热闹”——原来那不是非要凑“好”字的执念,是怕大宇上大学后,家里太空。 她总说大宇跟她不亲,青春期的男孩话少,关起门来就是游戏和习题,可每次大宇晚归,她都会在阳台站到深夜,手里攥着他初中时得的三好学生奖状。 现在病房里那个小的,皱巴巴的像只小猫,姐夫红着眼圈蹲在这儿,不是不欢喜,是后怕——怕那个说要“热闹”的人,差点没从手术台上下来。 护士推着婴儿车出来喂奶,小家伙哭得响亮,姐夫蹭地站起来,手忙脚乱想去接,又怕碰坏了似的缩回来。 以后的日子肯定难,大宇的学费,小的奶粉钱,姐姐的身体恢复——可他眼里那点慌里慌张的光,倒比“欢喜”实在多了。 或许人活着,就是折腾这些“怕”和“盼”吧。 保温桶里的鸡汤还热着,我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进去看看吧,她该醒了。”
我姐45岁非要生二胎,昨天刚生了个儿子,姐夫在病房门口蹲着眼圈都红了,哪有半点当
昱信简单
2025-12-14 00:50:27
0
阅读:31